夜上受降城闻笛
唐诗篇名。七绝。李益作,见《全唐诗》卷二八三。受降城,有东、中、西三城,此指西受降城,故址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作于贞元元年至六年(785-790)期间,是时诗人在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天德军灵盐丰夏等州节度使杜希全幕府中任职。该诗写久戍边地将士的思乡之情:“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前两句写登城所见月下景色,后两句言笛声勾起征人的乡思。全诗融诗情、画意、音乐美于一炉,无一字直接抒写乡思,而笔笔传情,具空灵蕴藉之妙。明王世贞赞曰:“‘回乐峰前’一章,何必王龙标、李供奉。”(《艺苑巵言》卷四)清施补华评云:“意态绝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百读不厌也。”(《岘傭说诗》)沈德潜称之为“绝唱”(《唐诗别裁》卷二○)。在当时即被谱入弦管,天下传唱(见《旧唐书·李益传》)。诗中“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句,承上启下,转折巧妙,为神来之笔。刘禹锡《和令狐相公言怀寄河中杨少君》诗中提到李益时,有“边月空悲芦管秋”句,即指此句。后宋代柳永词《倾杯》中“何人月下临风处,起一声羌笛”句子,亦由此句演化而来。
夜上受降城闻笛
[1]这是李益的名诗。受降城,当是西受降城,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李益(公元748~827),字君虞,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大历四年进士,曾在幽州节度使幕府任职,居边塞十多年。后召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官终礼部尚书。他的边塞诗负有盛名,尤以七绝见长,多为时人谱入乐府歌唱。《全唐诗》录存其诗二卷。
[2]“回乐烽”二句:回乐烽,指回乐县城附近的烽火台。回乐县,在今宁夏灵武西南。烽,一本作“峰”,误。二句写登受降城所见景色,黄沙似雪,皓月如霜,构成边塞荒寒苦寂意象。
[3]“不知”二句:芦管,芦笛。西域管乐器。管,一本即作“笛”。夜风送来凄凉的芦笛声,不知什么人在何处吹的,触动了所有征人的心绪,彻夜都远望家乡。
本诗写边塞将士的思乡情,未直写思乡,而绵绵乡情尽在诗中。前二句通过景色描写作铺垫,三句以西域特有的幽怨激越的芦笛声为线索,前三句将势蓄足,而末句仍不直写思乡,而拟写征人尽望乡的情节,语尽而意未尽。在全诗中色、声、情融为一体,互相激荡推进,构成一个艺术整体,意境深沉,含蕴不尽。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回乐烽’一章,不亚于王昌龄、李白。”胡应麟《诗薮》则说:“中唐绝,‘回乐烽前’为冠。”这首诗的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凄婉低沉风格,可以代表中唐边塞诗的特点。历代不少评论家推许这首七绝是中唐绝句中最好的一首。
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1。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2
【释】
1.回乐烽:指回乐县烽火台。回乐县属灵洲,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烽:又作“峰”。受降城:据《旧唐书·张仁愿传》记载,唐神龙三年张仁愿为防突厥而筑中、东、西三受降城。此处指西受降城。下:一作“外”,又有作“上”。
2.芦管:胡人乐器。《乐书》:“芦管之制,胡人截芦为之……出于北国者也。”
【译】
回乐烽前白沙似雪,
受降城下月华如霜。
是谁吹起哟,那悠悠的芦管,
三十万征人哟,一夜回首都望乡。
【评】
此诗为李益边塞诗代表作。明人胡应麟评其为中唐绝句之冠:“中唐绝‘回乐烽前’为冠”(《诗薮·内编》卷六);清人施补华评此诗与王昌龄之“秦时明月”等为边塞名作:“‘秦时明月’一首,‘黄河远上’一首,‘天山雪后’一首,‘回乐烽前’一首,皆边塞名作,意态绝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百读不厌也。”(《岘佣说诗》)
近人俞陛云则对此艺术作了具体分析:“对苍茫之夜月,登绝塞之孤城,沙明讶雪,月冷凝霜,是何等悲凉之境。起笔以对句写之,弥见雄厚;后二句申足二意,言荒沙万静之中闻芦管之声,随朔风而起,防秋多少征人,乡愁齐赴,则己之郁伊善感,不待言矣。”(《诗境浅说续编》)
首句讶沙明似雪,次句答以月明出霜,正为一体,万里澄清,宇宙无垠,正是边塞雄阔境之写照,芦管悲音,正是惹逗乡愁之契机。故全诗有“情思悱恻,百读不厌”之妙趣。
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烽前沙似雪, 受降城下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 一夜征人尽望乡。
这是写边塞将士乡情的七绝,是后世传诵的名作。
诗中的受降城,到底指何处?有歧说,多数注家认为是唐高宗(李治)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所筑的东、西、中三城中的“西城”(即今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东城,在今托克托县南,中城在内蒙包头市西)。也有不同说法,是指唐太宗亲临受降(突厥归降)的灵州治所回乐县的别称。因为这里是防御吐蕃、突厥的前线。(详见《唐诗赏析辞典》)
* * * *
这首诗,前二句写景,第三句写声,末句写情。
先看前二句——写景: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
回乐烽,即回乐县附近的烽火台,县故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烽,原作“峰”,误。
这两句写登城所见的月下景色:远望回乐城东西数十里的丘陵上,耸立一排烽火台;丘陵下是一片沙土,在朗月映照下,有如千里之白雪。近看高城之外,天地间尽是皎洁的月光,有如秋霜,令人见而生寒。
接着第三句——写声:
不知何处吹芦管?
芦管,即胡笳。《太平御览》引《晋先蚕仪注》云:“笳者,胡人卷芦叶吹之以作乐也,故谓曰胡笳。”此代指笛。这是说,在静夜里,寒风送来了凄凉哀怨的芦笛声。这为下边描写征人情思创造了典型环境。前边的写“景”和这里的写“声”,都为了末句直接抒情作烘托与铺垫。
最后一句——写情:
一夜征人尽望乡。
征人,即驻守边疆的士兵。这时,这些苦寒戍守边地的将士们是什么心境呢?诗歌告知大家:尽望乡。这个“望乡之思”,就在上述浓烈氛围下催生了出来,乡情绵绵,哀怨不尽。在这里,诗人化用晋人“刘琨登楼清啸”的典事。据《晋书·刘琨传》载:“(琨)在晋阳,尝为胡骑所围,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半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
此诗将景、色、声、情组成完整的艺术境界,显得精简空灵,又含有不尽之意。因此,为人们谱入管弦,传唱天下,成为中唐绝句的上乘之作。明人王世贞曾赞说:“绝句,李益为胜,‘回乐烽’一章,何必王龙标(昌龄)、李供奉(太白)?”但誉之未免略过一些。
夜上受降城闻笛
李益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李益早年由于官场失意,曾浪游燕赵一带,并在军中干过事。在那个连年征战的时代,他对边塞生活有亲身体验,这成为他诗作的突出题材。他的边塞题材的七言绝句,当时就被谱入管弦,广泛流行。后人一直认为他可以追踪李白、王昌龄。
“受降城”是武则天景云年间,朔方军总管张仁愿为抵御突厥的入侵而筑的,共三座。中城在朔州,西城在灵州,东城在胜州。诗中提到的“回乐(县)”,故城位置在今甘肃灵武县西南。据此,这里的受降城当指西城。杜甫有“韩公(指张仁愿)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的诗句,可见筑城原是为了国防。然而安史乱后,征战频仍,藩镇割据,国防力量削弱,杜甫已有“胡来不觉潼关隘”的叹息。到李益时,局面不但没有好转,政治危机反而进一步加深,边疆也不得安宁。战士长期驻守,长期不能还乡,厌战情绪普遍。
诗的一、二句写登楼所见。万里沙漠和矗立的烽火台,笼罩在朦胧的月色里。月照沙上,明晃晃仿佛积雪,城外地面也象铺上一层白灿灿的霜,令人凛然生寒。边塞物候与内地迥乎不同。江南秋夜,月白风清;而塞外尘沙漫天,连月夜也是昏惨惨的。在久戌不归的兵士心中,该会唤起怎样一种感情?背乡离井,独为异客的人,团𪢲明月往往唤起他对亲友的思念;而由月光联想到冰霜,更增添几分寒意,这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错乱,更是一种心理作用。前面介绍的李白的《静夜思》,也是写这样的心情,可以参阅。
这两句除掉地名方位,写景就在六个字:“沙似雪”、“月如霜”,却似图画一样的生动、鲜明。使人如身临其境,感受到边塞大漠月夜全部的苍凉。诗人何以能以极省的笔墨造成丰富的形象呢?这是因为语言艺术塑造形象,不同于绘画,它不是象绘画那样详尽到每一个细节;其塑造形象是依靠语言典型化的作用,因而比之绘画,具有更大概括性。当它抓住对象最有特征的细节予以刻划,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契诃夫曾说过:如果很好写出一个碎玻璃的反光等等,就能写出整个月夜。诗人抓住“沙似雪”、“月如霜”,这样最有边塞特征的景色,就把整个塞上的单调、凄凉气氛表现出来了,达到了最经济的语言效果。
第三句写登楼所闻。紧承上两句而来。登楼者对着凛然生寒的大漠月色,难以禁持时,寒风忽然吹来一阵凄怨的笛声。“芦管”本是胡笳声别名。但诗题已明说“闻笛”,可见此处“芦管”指的就是笛。因为在荒漠的景色中,诗人听到的笛声,萧瑟凄凉,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简直与幽咽哀怨的胡笳声相似。夜里寂静,而夜晚人的听觉最敏锐,因此,夜声给人的感觉印象也最深,造成的心理影响特别大。笛声随风而至,时断时续,所以说“不知何处”。这同时也表明登楼者在仔细倾听,心揪得更紧。
前三句对塞景边声的渲染,直接引起第四句。这句抒情,妙在一个“尽”字,诗人并不就此把思乡之情局限于一身,而是推及所有的“征人”。也就是和《从军北征》所谓“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一个意思。诗人心事浩茫,想到此夜塞上何处无月?何处无征人?谁看到这如霜的月光不思家?谁听到这幽怨的笛声不下泪?厌战思归的心理,何止登楼者一己而已!这一个“尽”字,就把诗境大大深化,不但渗透诗人深刻的生活体验,而且容纳了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使诗歌艺术形象升华,获得了典型性。
夜上受降城闻笛
李益
回乐烽前沙似雪①,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②,一夜征人尽望乡。
【解题】
此诗约作于贞元元年(785)后,时李益在朔方天德军节度使杜希全幕中。受降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朔方军总管张仁愿于黄河以北筑东、西、中三受降城,用以防御突厥侵扰。此处当指西受降城,故址在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北。诗中前二句写夜上受降城所见景色,后二句写征人闻笛声而引起的怀乡之情。情景声色融合一体,气象阔大,意境悲壮,未有衰飒情调。故在当时就被推重,谱人乐府传唱。施补华《岘傭说诗》云:“意态绝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百读不厌也。”
【注释】
①回乐烽:回乐县的烽火台,县故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烽一作“峰”,误。②芦管:即芦笛,以芦制成的管乐器。
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上月如霜。”诗人登上受降城 (回乐县和受降城故址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但见黄沙似雪,冷月如霜; 烽火台前,回乐城外,白光一片,寒气逼人。这两句表现出大漠的荒寒寥廓,戍守将士心境的寂寞凄凉。“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在这样的氛围中,忽然听到了不知从何而来的芦笛声,那凄凉幽怨、如泣如诉之音,深深地触动了将士们的思乡之情。这里,“不知”表现征人的迷惘,“一夜”和“尽望”,点出所有征人都在思乡,思绪持续了整夜。诗人不直接抒写乡情,却用一个拟想中征人望乡的镜头来表现。情寓景中,含蓄有味。
短短一首小诗,有情有景,有色有声,节奏和谐,音调响亮,所以当时就被乐工争相传唱。
- 原文
- 拼音
- 繁体
- 《夜上受降城闻笛》.[唐].李益.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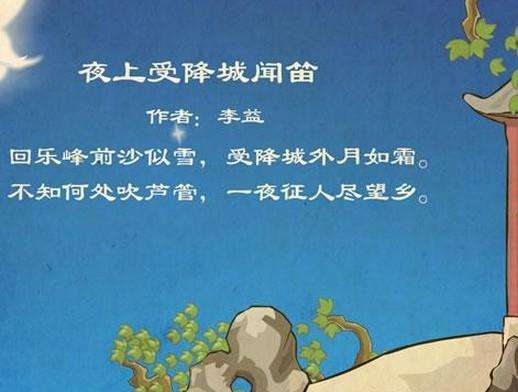
- 《 yè shànɡ shòu xiánɡ chénɡ wén dí 》《 夜 上 受 降 城 闻 笛 》.[ tánɡ ]. lǐ yì..[ 唐 ]. 李 益.huí lè fēnɡ qián shā sì xuě , shòu xiánɡ chénɡ xià yuè rú shuānɡ 。回 乐 峰 前 沙 似 雪 , 受 降 城 下 月 如 霜 。bù zhī hé chù chuī lú ɡuǎn , yí yè zhēnɡ rén jìn wànɡ xiānɡ 。不 知 何 处 吹 芦 管 , 一 夜 征 人 尽 望 乡 。
- 《夜上受降城聞笛》.[唐].李益.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 译文
- 注释
- 诗评
- 【译文】 回乐烽前,沙海似雪无垠;受降城下,明月清冷如霜;不知在哪儿,有人吹起了芦管; 这漫漫长夜里,远在塞外的征人哟,全都在遥念自己的故乡!
【逐句翻译】回乐烽前沙似雪,回乐烽前的沙原皑皑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受降城外的月光皎皎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不知何处呜呜呜吹奏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撩拨得征人一夜尽望故乡。 - ①受降城:即灵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灵武县。贞观二十年(646), 唐太宗亲临灵州接受突厥一部的投降,故称灵州为受降城。唐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所 筑之三受降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黄河的北面,与唐太宗受降的灵州无关。
②回乐 烽:即回乐县附近的烽火台。回乐县,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西南。李益另有《暮 过回乐烽》:“烽火高飞百尺台,黄昏遥自碛西来。昔时征战回应乐,今日从军乐未回。” 结句颠倒“回乐”二字,颂今从军之乐,别有新意。
③芦管:乐器名。截芦为之,与觱篥 相类,状似胡笳。(参阅《文献通考·乐·芦管》) - 【集评】
明·王士贞:“绝句李益为胜,……《回乐烽》一章,何必王龙标、李供奉?”(《艺苑卮言》卷四)
明·胡应麟:“中唐绝 ‘回雁(乐)烽前’ 为冠。”(《诗薮·内编》卷六)
清·施补华:“‘秦时明月’一首,‘黄河远上’一首,‘天山雪后’一首,‘回乐烽前’一首,皆边塞名作,意态健绝,音节高亮,情思绯恻,百读不厌也。”(《岘佣说诗》)
近·俞陛云:“对苍茫之夜月,登绝塞之孤城,沙明讶雪,月冷凝霜,是何等悲凉之境。起笔以对句写之,弥见雄厚;后二句申足二意,言荒沙万静之中闻芦管之声,随朔风而起,防秋多少征人,乡愁齐赴,则己之忧伊善感,不待言矣!”(《诗境浅说续编》)
其《受降城闻笛》诗,教坊乐人取为声乐度曲,又有写《征人歌》、《早行篇》为图画者,“回乐烽前沙似雪”之诗是也。(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绝句李益为胜,“回乐烽”一章,何必王龙标、李供奉? (王世贞《艺苑卮言》)征人望乡,只加一“尽”字,而征戍之苦,离乡之久,胥包孕在内矣。 (李锳《诗法易简录》)对苍茫之夜月,登绝塞之孤城,沙明讶雪,月冷疑霜,是何等悲凉之境!起句以对句写之,弥见雄厚。后二句申足上意,言芦管之声,随朔风而起,防秋多少征人,乡愁齐赴,则己之郁伊善感,不待言矣。李又有《从军北征》诗,意境略同。此诗有夷宕之音,《北征》诗用伉爽之笔,均隹构也。(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
- 赏析一
- 赏析二
- 赏析三
- 李益是中唐边塞诗的代表诗人,他早岁从军,驻守边境,“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从军诗序》),写下了大量的边塞诗。由于时代风气影响所致,他的边塞诗虽不乏抑扬壮阔的格调, 但已不复有盛唐边塞诗那种慷慨激昂、建功边塞的豪情, 而带上了一重感伤衰飒的气氛。抑扬壮阔与感伤衰飒揉合在一起,这便是李益边塞诗的情思特色。《夜上受降城闻笛》就是一首体现这种感情基调的七绝诗。诗题中的 “受降城”,指位于唐代灵州的西受降城。贞观二十年,唐太宗曾亲临灵州接受突厥一部的投降,这便是受降城得名的由来。灵州治所在回乐县,其故城在今甘肃省灵武县西南,受降城即回乐县的别称。唐王朝自从安史乱后,国防力量大大削弱,边境不得安宁。将士长期驻守边陲,不能还乡同亲人团聚,厌战思乡情绪普遍滋生。诗人对此有亲身体验,对征人的思乡心理, 感受特别深切。在一个月夜里, 他登上受降城楼, 面对边塞夜色, 不禁感慨万端, 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诗篇。诗的一、二句写登楼所见的边塞夜景。诗人登上回乐城楼,首先吸引他注意的,是那战争的报警装置——烽火台,以及烽火台前的一片象冬雪一样洁白而泛着寒光的沙漠;再回身四望,高城内外、天上地下洒满皎洁的月光,尤如铺上了一层白灿灿的秋霜, 令人望而生寒。这一联写景虽然气象阔大,但诗人以雪喻沙、以霜拟月, 则说明这是战争间歇边塞之夜的特有景色。它是那样的空旷而死寂,凄神寒骨,令人不可久居。它对于久戍不归的诗人和众将士,又是一个多么寂寞难挨的夜晚?这两句写景虽不及言情,但已渗透了诗人感伤沮丧的心绪,为下文抒写望乡之情作了环境的铺垫。第三句接写登楼所闻。当诗人面对着万籁俱寂的大漠夜色正难以禁持时,寒风忽然吹送来一阵凄怨的笛声。“芦管”本是胡茄别名,但诗题已明说 “闻笛”,可见此处“芦管”指的就是笛。这萧瑟凄凉、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笛声是引发征人思乡的触媒:或许是“羌笛何须怨杨柳”,令征人想起折柳相送、依依惜别的亲人;或者是“撩乱边愁听不尽”,让征人感叹边塞生活的艰难。这笛声随风而至,时断时续,“不知何处”而来,表明征人在侧耳倾听,仔细辨别笛声的方向和内涵,并暗示出听笛人怔忡、怅惘的心情。前三句对边塞夜色、笛声的渲染, 为思乡的主题层层蓄势,逼出了石破天惊的最末一句:“一夜征人尽望乡。”诗人没有采取直接抒情的方式,而是塑造出征人“望乡”的群象,尤如电影镜头的“定格”,将征人思乡的心理定势用形象的画面突现在读者眼前,有力地突出了征人思乡的主题。“一夜”说明思乡之久, 不仅彻夜难眠, 甚至夜复一夜、日复一日无时不在思乡。“尽”字概括了所有的征人,值此孤寂之夜,谁不思家?闻此幽怨之笛,谁不下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诗人对边塞生活的独特感受同征人们的普遍心理融为一体,使这首诗获得了高度典型的社会意义,赢得了时人的共鸣, 所以此诗一出, “天下亦唱为乐曲” (《唐国史补》)。管世铭曾说:“李庶子绝句,出手即有羽歌激楚之音,非古之伤心人不能及此。”(《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他正确地指出了李益诗中悲壮声情感人至深的原因。此诗因景及情,将苍茫寥廓的景色同感伤衰飒的情思结合在一起,完全写出了征人的眼前之景、心中之事,堪称中唐七绝诗的名篇。明代诗论家胡应麟曾举此篇为例评说: “七言绝, 开元之下, 便当以李益为第一。”(《诗薮》)这一评价,李益是当之无愧的。
- 这首绝句,抒写征人久戍思归的怨望心情。诗的开头两句,以粗大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寥廓荒寒的边地月夜图景。登楼远望,回乐城周围数十里的山丘上,耸立着一排烽火台。烽火台下是一片沙地,沙子在月光的映照下,晶莹洁白如积雪,周遭寒气袭人。高城之外,天空悬挂着一轮明月,月光洒向大地,更觉凄冷。这如雪的沙漠和如霜的月光,空寂冷漠,正是触发戍边将士思乡之情的典型环境。在如此静穆的夜境中,又突然出现了凄怨的芦笛之声,这就很自然地引起了征人的无限乡思。笛声本是凄清,远离乡关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听到,更觉哀怨不尽。“不知何处”四字,有闻者惊心动容,苦不胜情之意。末句点出“望乡”正意,用拟想中的征人尽望乡的特写镜头,展现了一幅凄苦哀怨的动人场景。“一夜”和“尽”都是着意强调。形象鲜明,意境高远。前人曾说,李益的七绝,是学王昌龄的。这首绝句的形象完整丰富,韵味含蓄深长,音韵和谐宛转,语言精炼自然,都接近王昌龄。但这首诗已经没有盛唐边塞诗那种乐观豪放的情调,即使和王昌龄《从军行》中描写“边愁”的诗相比,李益诗也是凄凉感伤而缺少雄浑悲壮。这是时代使然,李益从军所到的幽州、河朔等地,中唐时代已成为藩镇割据的地方。这里的边塞士卒们,迫于连年不断的内外战争,卫国立功的英雄气概已黯然消失。因而诗人主要抒写士卒们的久戍思归的怨望心情,就不是偶然的了。唐初朔方军总管张仁愿所筑受降城,有东、西、中三城,皆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本诗所指的是西城还是中城,历来注家说法不一。回乐峰指回乐县的烽火台,回乐县故址在今甘肃灵武县西南。
- 这是写边塞将士乡情的七绝,是后世传诵的名作。
诗中的受降城,到底指何处?有歧说,多数注家认为是唐高宗(李治)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所筑的东、西、中三城中的“西城”(即今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东城,在今托克托县南,中城在内蒙包头市西)。也有不同说法,是指唐太宗亲临受降(突厥归降)的灵州治所回乐县的别称。因为这里是防御吐蕃、突厥的前线。(详见《唐诗赏析辞典》)* * * *
这首诗,前二句写景,第三句写声,末句写情。
先看前二句——写景: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
回乐烽,即回乐县附近的烽火台,县故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烽,原作“峰”,误。
这两句写登城所见的月下景色:远望回乐城东西数十里的丘陵上,耸立一排烽火台;丘陵下是一片沙土,在朗月映照下,有如千里之白雪。近看高城之外,天地间尽是皎洁的月光,有如秋霜,令人见而生寒。
接着第三句——写声:
不知何处吹芦管?
芦管,即胡笳。《太平御览》引《晋先蚕仪注》云:“笳者,胡人卷芦叶吹之以作乐也,故谓曰胡笳。”此代指笛。这是说,在静夜里,寒风送来了凄凉哀怨的芦笛声。这为下边描写征人情思创造了典型环境。前边的写“景”和这里的写“声”,都为了末句直接抒情作烘托与铺垫。
最后一句——写情:一夜征人尽望乡。
征人,即驻守边疆的士兵。这时,这些苦寒戍守边地的将士们是什么心境呢?诗歌告知大家:尽望乡。这个“望乡之思”,就在上述浓烈氛围下催生了出来,乡情绵绵,哀怨不尽。在这里,诗人化用晋人“刘琨登楼清啸”的典事。据《晋书·刘琨传》载:“(琨)在晋阳,尝为胡骑所围,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半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
此诗将景、色、声、情组成完整的艺术境界,显得精简空灵,又含有不尽之意。因此,为人们谱入管弦,传唱天下,成为中唐绝句的上乘之作。明人王世贞曾赞说:“绝句,李益为胜,‘回乐烽’一章,何必王龙标(昌龄)、李供奉(太白)?”但誉之未免略过一些。
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1。不知何处吹芦管2,一夜征人尽望乡。
【校记】
1.下,《全唐诗》一作“外”。
2.管,《全唐诗》一作“笛”。
【注释】
[受降城] 唐代受降城有东、西、中三座城,武后景云年间朔方军总管张仁愿所筑,此处指西受降城,在今临夏灵武。《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东受降城,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汉定襄郡之盛乐县也,后魏都盛乐,亦谓此城。武德四年平突厥,于此置云州,贞观二十年改为云州都督府,麟德三年改为单于大都护府,垂拱二年改为镇守使,圣历元年改置安化都护,开元七年隶属东受降城,八年复置单于大都护府。”“东受降城,本汉云中郡地,在榆林县东北八里,今属振武节度。”“中受降城,本汉九原郡地,汉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开元十年于此城置安北大都护府,后又移徙。”“西受降城,在丰州西北八十里,盖汉朔方郡地,临河县故理处。开元初为河水所坏,至开元十年总管张说于故城东别置新城。今城西南隅又为河水所坏。”“三受降城,景云三年张仁愿所置也。”按:《全唐诗》卷二八三亦收有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一作戎昱诗):“入夜思归切,笛声清更哀。愁人不愿听,自到枕前来。风起塞云断,夜深关月开。平明独惆怅,落尽一庭梅。”
[回乐峰] 回乐县境内的一个山峰。回乐县唐属灵州,为朔方节度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灵州”:“《禹贡》雍州之域。春秋及战国属秦,秦并天下为北地郡。汉时为富平县之地,后汉安帝永初五年,西羌大扰,诏令郡人移理池阳。顺帝永建四年归旧土。其城赫连勃勃所置果园,今桃李千余株,郁然犹在。后魏太武帝平赫连昌,置薄骨律镇,后改置灵州。以州在河渚之中,随水上下,未尝陷没,故号‘灵州’。周置总管府,隋大业元年罢府为灵州,三年又改为灵武郡,武德元年又改为灵州,仍置总管,七年改为都督府。开元二十一年,于边境置节度使,以遏四夷,灵州常为朔方节度理所。”“回乐县,本汉富平县地,属北地郡,在今县理西南富平故城是也。后汉置回乐县,枕黄河,后魏刁雍为薄骨律镇将,上表请开富平西三十里艾山旧渠,通河水,溉公私田四万余顷,人大获其利。”
[芦管] 即芦笳。古代的一种管乐器。以芦叶为管,管口有哨簧,管面有音孔,下端范铜为喇叭嘴状,吹时用指启闭音孔,以调音节。宋曾慥《类说·集韵》:“胡人卷芦叶而吹,谓之芦笳。”唐元稹《遣行》其九:“猿声芦管调,羌笛竹鸡声。”
【评论】
《艺苑卮言》卷四:绝句李益为胜,“回乐峰前”一章,何必王龙标、李供奉?
《诗薮内编·近体下·绝句》:初唐绝,“蒲桃美酒”为冠,盛唐绝,“谓城朝雨”为冠;中唐绝,“回乐峰前”为冠;晚唐绝,“清江一曲”为冠。“秦时明月”在少伯自为常调,用修以诸家不选,故《唐绝增奇》首录之。所谓前人遗珠,兹则掇拾。于鳞不察而和之,非定论也。
《唐诗合选评解》卷四:沙飞月皓,举目凄凄,于此间而闻笳声,安有不念切乡关者也。苏东坡曰:七言绝,开元以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可与太白、少伯竞爽。沈归愚曰:音节神韵,可追龙标、供奉。七言绝,中唐以李庶子、刘宾客为最。
《说诗晬语》卷上:李沧溟推王昌龄“秦时明月”为压卷,王凤洲推王翰“蒲萄美酒”为压卷,本朝王阮亭则云:“必求压卷,王维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龄之‘奉帚平明’,王之涣之‘黄河远上’,其庶几乎!而终唐之世,亦无出四章之右者矣。”沧溟、凤洲主气,阮亭主神,各自有见。愚谓:李益之“回乐峰前”,柳宗元之“破额山前”,刘禹锡之“山围故国”,杜牧之“因笼寒水”,郑谷之“扬子江头”,气象稍殊,亦堪接武。
《重订唐诗别裁集》卷二○:《夜上受降城闻笛》:明云“芦管”。芦管,笳也,“笛”字应误。又:绝唱。
《唐诗摘抄》卷四朱之荆补评:沙飞月皎,举目凄凄,于此而闻笛声,安有不思乡念切者。
《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唐人万首绝选批校》:高格、高韵、高调,司空侍郎所谓“反虚入浑”者。
《诗境浅说》续编:对苍茫之夜月,登绝塞之孤城,沙明讶雪,月冷疑霜,是何等悲凉之境。起笔以对句写之,弥见雄厚。后二句,早足上意,言荒沙万静中,闻芦管之声,随朔风而起,防秋多少征人,乡愁齐赴,则己之郁伊善感,不待言矣。李诗又有《从军北征》云:“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意境略同,但前诗有夷宕之音,《北征》诗用抗爽之笔,均佳构也。
【评论】
李益《从军诗序》:君虞始长八岁,燕戎乱华。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故其为文,咸多军旅之思。自建中初,故府司空巡行朔野,迨贞元初,又忝今尚书之命,从此出上郡、五原四五年,荏苒从役。其中虽流落南北,亦多在军戎。凡所作边塞诸文,及书奏余事,同时幕府选辟,多出词人。或因军中酒酣,或时塞上兵寝,相与拔剑秉笔,散怀于斯文。率皆出于慷慨意气,武毅犷厉。本其凉国,则世将之后,乃西州之遗民与?亦其坎壈当世,发愤之所致也。时左补阙卢景亮见知于文者,令余辑录,遂成五十首赠之。
《诗人主客图》:清奇雅正主:李益。
《全唐诗话·李益》:益,姑臧人,字君虞。大历四年登第。其《受降城闻笛》诗,教坊乐人取为声乐度曲。又有写征人歌、早行诗为图画者,“回乐峰前沙似雪”之诗是也。益有心疾,不见用。及为幽州刘济营田副使,献诗有“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之句,左迁右庶子。年且老,门人赵宗儒自宰相罢免,年七十余。益曰:“此我为东府所选进士也。”闻者怜益之困。后迁礼部尚书,致仕,卒。
《全唐诗话·刘鲁风》:自贞元后,唐文甚振,以文学科第为一时之荣。及其弊也,士子豪气骂吻,游诸侯门,诸侯望而畏之。如刘鲁风、姚嵓杰、柳棠、胡曾之徒,其文皆不足取。余故载之者,以见当时诸侯争取誉于文士,此盖外重内轻之牙蘖。如李益者,一时文宗,犹曰:“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其后如李山甫辈,以一名一第之失,至挟方镇,动宰辅,则又有甚焉者矣。一篇一韵,初若虚文,而治乱之萌系焉。余以是知其不可忽也。
《临汉隐居诗话》:韦应物古诗胜律诗,李德裕、武元衡律诗胜古诗,五字句又胜七字。张籍、王建诗格极相似,李益古律诗相称,然皆非应物之比也。
《沧浪诗话·诗评》:大历以后,我所深取者,李长吉、柳子厚、刘言史、李德舆、李涉、李益耳。
《后村诗话后集》卷一:卢纶、李益善为五言绝句,意在言外。纶《伤秋》云:“岁去人头白,秋来树叶黄。搔头向黄叶,与尔共悲伤。”《宫词》云:“玉砌红花树,香风不敢吹。春风解天意,偏发殿南枝。”学士院春帖子可用。又云:“辞辇复当熊,倾必奉六宫。君王若看貌,甘在众妃中。”益《送人》云:“路旁一株柳,此路向延州。延州在何处,此咱起悠悠。”《照镜》云:“衰鬓朝临镜,相看各自疑。惭君明似月,照我白如丝。”《阳城烽舍》云:“何地可潸然,阳城烽树边。今朝望乡客,不饮北流泉。”皆有无穷之味。刘幽求,功业人,不以诗名,其五言云:“心为明时尽,君门尚不容。田园芜没尽,归去乐何从。”《裴晋公题太原厅壁》云:“危事经非一,浮云的是空。白头官舍里,今日又春风。”皆微婉不刻露。顷选绝句,或未见全集,或偶漏落,可收入也。《石林避暑录》载楚州紫极宫壁间诗云:“宫门闲一入,独凭阑干立。终日不逢人,朱顶鹤声急。”亦可收。
《后村诗话新集》卷三:卢、李中表兄弟,诗律齐名,其五七言妙绝者已选入《绝句》。然两生皆从军出塞,他诗可脍炙传诵者,人多容易看过,余既耄耋,悉录于篇以备遗忘。
《唐才子传·李益》:风流有辞藻,与宗人贺相埒……往往鞍马间为文,横槊赋诗,故多抑扬激厉悲离之作,高适、岑参之流也。
《升庵诗话·晚唐两诗派》:马戴、李益不坠盛唐风格,不可以晚唐目之。数君子真豪杰之士哉。
徐献忠《唐诗品》:君虞生习世纷,中遭顿抑,边朔之气,身所经闻。故从军、出塞之作,尽其情理,而慕散投林,更深遐思。古诗郁纡盘薄,姿态变出,自非中唐之致。其七言小诗,与张水部作等,亦国风之次也。
《艺苑卮言》卷四:绝句,李益为胜,韩翃次之。
又:岑参、李益诗语不多,而结法撰意雷同者几半。始信少陵如韩淮阴、多多益办耳。
《诗薮内编·古体下》:李杜外,短歌可法者:岑参《蜀葵花》、《登邺城》,李颀《送刘昱》、《古意》,王维《寒食》,崔颢《长安道》,贺兰进明《行路难》,郎士元《塞下曲》,李益《促促曲》、《野田行》,王建《望夫石》、《寄远曲》,张籍《节妇吟》、《征妇怨》,柳宗元《杨白花》,虽笔力非二公比,皆初学易下手者。但盛唐前,语虽平易,而揭雍容;中唐后,语渐精工,而揭促迫,不可不知。
《诗薮内编·近体下》:中唐绝,如刘长卿、韩翃、李益、刘禹锡,尚多可讽咏。
又:七言绝句以太白、江宁为最,参以王维之俊雅,岑参之浓丽,高适之浑雄,韩翃之高华,李益之神秀,益以弘、正之骨力,嘉、隆之气韵,集长舍短,足为大家。上自元和,下迄成化,初学姑置可也。(晚唐绝句易入人,甚于宋、元之诗,故尤当戒。)
又:七言绝,开元之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龙标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
《诗薮续编·国朝下》:唐人称乐天广大教化主,李益清奇雅正主,二子不足当,谓两琅琊可耳。
《诗源辩体》卷二二:五言古多六朝体,效永明者,酷得其风神。七言古,气格绝类盛唐。《塞下曲》本一首,今集中作四绝句者,非。《祝殇辞》语多奇警,与李华《吊古战场文》并胜,惜非完璧。五言律,气格亦胜。“白马羽林儿”一篇,可配开宝。“霜风先独枝,瘴雨失荒城”一联,雄伟亦类初唐。七言绝,开宝而下足称独步。胡元瑞云:“七言绝,开元之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龙标竞爽。”
又:李益、权德舆在大历以后,而其诗格有类盛唐者,乃是其气质不同,非有意复古也。
《唐音癸签·评汇三》:李君虞(益)生长西凉,负才尚气;流落戎旃,坎壈世故。所作从军诗,悲壮宛转,乐人谱入声歌,至今诵之,令人凄断。
《唐音登签·谈丛二》:唐人诗谱入乐者,初、盛王维为多,中、晚李益、白居易为多。
《诗镜总论》:李益五古,得太白之深,所不能者澹荡耳。太白和有余闲,故游衍自得。益将矻矻以为之。《莲塘驿》、《游子吟》自出身手,能以意胜,谓之善学太白可也。
《带经堂诗话·总集门四·自述类上》:弇州先生曰:七言绝句盛唐主气,气完而意不必工;中唐主意,意工而气不必完。予反复斯集,益服其立论之确。毋论李供奉、王龙标暨开元、天宝诸名家,即大历、贞元间如李君虞、韩君平诸人,蕴藉含蓄,意在言外,殆不可及。
《载酒园诗话又编·李益》:中唐人故多佳诗,不及盛唐者,气力减耳。雅澹则不能高浑,雄奇则不能沉静,清新则不能深厚。至贞元以后,苦寒、放诞、纤缛之音作矣。惟李君虞风气不坠,如《竹窗闻风》、《野田行》,俱中朝正始之音。余尤爱其入情之句,如《游子吟》:“莫以衣上尘,不谓心如练。”《杂曲》:“爱如寒炉火,弃若秋风扇。山岳起面前,相看不相见。”“尝闻生别离,悲莫悲于此。同器不同荣,堂下即千里。”殊有汉魏乐府之遗。《效古促促曲为河上思妇作》曰:“促促何促促,黄河九回曲。嫁与棹船郎,空林将影宿。不道君心不如古,那令妾貌长如玉。”读此觉李嘉祐“花落黄鹂不复来,妾老君心亦应变”,下语殊浅。但君虞能体贴人情至此,何以使业衔冤,崇敬生劫?
又:李以边辞名。余以“边马枥上惊,雄剑匣中鸣”,犹未足奇,如《再赴渭北使府留别》曰:“报恩身未死,识路马还嘶。”信为悲壮。
《重订唐诗别裁集》卷二○:七言绝句,中唐以李庶子、刘宾客为最,音节神韵,可追逐龙标、供奉。
《石洲诗话》卷二:中唐六七十年之间,除韦、柳、韩三家古体当别论,其余诸家,堪与盛唐方驾者,独刘梦得、李君虞两家之七绝,足以当之。
《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五古凡例》:大历五古,以钱仲文为第一,得意处宛然右丞。次即李君虞,得太白一体。
又《五绝凡例》:李君虞声情凄惋,尤篇篇可入管弦。
又《七绝凡例》:大历以还,韩君平之婉丽,李君虞之悲慨,犹有两王遗韵,宜当时乐府传播为多。李庶子绝句,出手即有羽歌激楚之音,非古伤心人不能及此。
张澍《李尚书诗集序》:昔开元时,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辈风尘未偶,贳酒小饮,值旗亭雨雪,梨园会宴,以歌诗之多寡,定名称之甲乙,揶揄欢噱,自鸣得意。何似君虞之篇,被诸管弦,供奉至尊,施乃图缋哉!独其宦途蹇偃,送士登庸怨望陵跞,为时排迮,又未尝不叹其狭中也。然迹汉以来,仲宣赋从军,只贡颂谀;灵运送秀才,徒述怀恩。惟君虞以爽飒之气,写征戍之情,览关塞之胜,极辛苦之状,当朔风驱雁,荒月拜狐,抗声读之,恍见士卒踏冰而皲瘃,介马停秣而悲鸣,讵非才之所独至耶?其他章句,亦清丽绝伦,宜与长吉齐名,无所愧让。而《征人》、《早行》诗,最推杰作,今已失传。知其散逸不少。
《越缦堂读书记·札记》:若论绝句,则李十郎之雄浑高奇,不特冠冕十子,即太白、龙标,亦当退让。
《岘佣说诗》:“秦时明月”二首,“黄河远上”一首,“天山雪后”一首,“回乐峰前”一首,皆边塞名作;意态绝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百读不厌也。
《三唐诗品》卷二:姑臧李益,字君虞,其源出于邱希范、吴叔庠而参宗于摩诘。长于托咏,朗润风华,正如落花依草,妞然妩媚。余作少衰,开晚唐之派。大历十人,固其杰也。
夜上受降城闻笛
李益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受降城,据载为唐神龙三年(707),中宗(李显)命张仁愿在黄河以北筑中、东、西三受降城,以拂云祠为中城。与东西两城相距各四百里左右,置烽候一千八百所,首尾相应,巩固了唐王朝的北部边疆。“回乐烽”,在今甘肃灵武县西南,诗中所写“受降城”,似当指西城。
前二句,借用比喻手法描写受降城周围夜色。诗人佇立城头,举目远眺,但见皓月如银,碧空万里,在回乐峰的山丘上,那座座烽火台下,连绵起伏的沙漠静静地沉浸在皎洁的月光里。望远方,沙漠上仿佛覆盖着团团白雪;近看,城外好象降下一层薄霜。这“雪”与“霜”同是用来形容月色,由于视觉的远近不同,故对月色的深淡程度的感觉也有别。而且,这种描写使人产生一种寒气袭人的凄凉悲苍之感。后二句,主要表现征人的思归情绪。在这万籁俱寂的月夜里,诗人的心头也仿佛蒙上了一层迷惘的薄纱。当夜风送来清凄而幽怨的笛声时,便立即牵动了征人们怀念故乡的情丝,使他们彻夜之间久久不能入睡。“不知”二字更是进一步强调思归的感情,希望通过笛声传送到遥远的家乡去。这是借物(声音)言情的具体表现。这种感情的表达,与他的《从军北征》诗中的“一时回首月中看”所描绘的情景基本类似,可参照阅读。
这首诗,总的说来是一、二句绘形,三句绘声,末句抒情。诗人通过景——声——情的相互烘托,相互融合,造成了一个诗情画意的生动艺术形象,令人赞不绝口。
《夜上受降城闻笛》ye shang shou xiang cheng wen di
Hearing a Barbarian Flute from Atop the Walls of Shouxiang Citadel at Night→李益(Li Yi)
- 殷永林是什么意思
- 殷汝耕是什么意思
- 殷汝耕是什么意思
- 殷汝耕是什么意思
- 殷汝耕是什么意思
- 殷汝骊是什么意思
- 殷汝骊是什么意思
- 殷汝骊是什么意思
- 殷汝骊是什么意思
- 殷洪纂息仕冓造像记是什么意思
- 殷浩是什么意思
- 殷浩是什么意思
- 殷浩是什么意思
- 殷浩是什么意思
- 殷浩是什么意思
- 殷浩书空是什么意思
- 殷浩北伐是什么意思
- 殷浩才略是什么意思
- 殷海光是什么意思
- 殷海国是什么意思
- 殷淑仪(殷氏)是什么意思
- 殷淳是什么意思
- 殷濂君是什么意思
- 殷炎麟是什么意思
- 殷炎麟是什么意思
- 殷焕先是什么意思
- 殷焕先是什么意思
- 殷焕先是什么意思
- 殷琪是什么意思
- 殷璠是什么意思
- 殷痕苦雨洗不落,犹带湘娥泪血腥是什么意思
- 殷登皋是什么意思
- 殷登翼是什么意思
- 殷皓是什么意思
- 殷碧霞是什么意思
- 殷礼征文是什么意思
- 殷秀岑是什么意思
- 殷秀岑是什么意思
- 殷秀岑是什么意思
- 殷秀岑是什么意思
- 殷章印是什么意思
- 殷章甫是什么意思
- 殷纪禹是什么意思
- 殷细宽是什么意思
- 殷绍礼是什么意思
- 殷维君是什么意思
- 殷致远是什么意思
- 殷良弼是什么意思
- 殷芸是什么意思
- 殷芸是什么意思
- 殷芸是什么意思
- 殷芸小说是什么意思
- 殷芸小说(辑注本)是什么意思
- 殷荫龙是什么意思
- 殷虚书契续绵是什么意思
- 殷虚书契考释是什么意思
- 殷虚书契考释是什么意思
- 殷虚卜辞综述是什么意思
- 殷虚卜辞综述是什么意思
- 殷虚文字甲编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