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鸟
《诗经·秦风》篇名。挽歌。《诗序》谓秦“国人”作。秦穆公死,命以奄息、仲行、鍼虎殉葬。三人皆子车氏之子, “国人”视为“良人”,故作此诗以悼之。全诗三章,分挽奄息、仲行、鍼虎三人,对其表示深切哀悼,客观上暴露了殉葬制度的罪恶。诗中写三人临穴殉葬时恐惧之状,历历如绘。
黄鸟
❶《诗经·秦风》篇名。《毛诗序》云:“《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序》说的史实依据是《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史记·秦本纪》:“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据此,“三良”乃被杀殉葬。而《郑笺》三良“自杀以从死”之解(“三家诗”说同),则与诗中“临其穴,惴惴其慄”的情景相违。这首挽歌共有三章,章十二句,分悼奄息、仲行、鍼虎三良。均以黄鸟哀鸣起兴,又以棘、桑、楚三字,谐音双关急、丧、痛楚。气氛悲怆,情调激越凄楚。
❷《诗经·小雅》篇名。《毛诗序》谓其“刺宣王也”。未说明所刺何事。朱熹《诗集传》则认为是“民适异国,不得其所,故作此诗”。今人多据此作进一步发挥,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黄鸟就是瓦雀,这和耗子是一样,也就是和坐食阶级一样,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的。痛恨本国的硕鼠,逃了出来,逃到外国又遇到一样的黄鸟。天地间哪里有乐土呢?倦于追求的人,他又想逃回他本国去了。”这一分析是切合诗旨的。此诗与《魏风·硕鼠》参看,可以想象出当时社会的昏暗荒乱和人民生活的极端困苦,有很强的现实性。其手法亦与《硕鼠》相同,以黄鸟起兴,用责问的语气,斥责黄鸟的“集于穀”“啄我粟”的丑恶行径,表现了诗人对于坐食阶级的厌恶心情,语言质朴有力,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黄鸟
(小雅·祈父)
黄鸟黄鸟,无集于榖,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榖。言旋言归,复我邦族。
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
此诗运用比拟手法,用“黄鸟”比剥削者,化抽象为形象。并且,采用反复唱叹的形式,三章中只有几个名词的更易,就把身在异邦遭受欺凌而怀念家乡亲人的复杂感情,表达得十分生动真切,层递深入,可谓以少总多,妙于变化。
《黄鸟》
交交黄鸟止于棘。
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维此奄息,百夫之特。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
谁从穆公?子车仲行。
维此仲行,百夫之防。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
谁从穆公?子车鍼虎。
维此鍼虎,百夫之御。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诗经·秦风》
这是一首哀悼殉葬者的挽诗。
《毛诗序》:“《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揭示了本诗的创作旨意和时代背景。而“哀三良,刺穆公”一说,也有着确凿的史实依据。据《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史记·秦本纪》写得更具体,说秦穆公死时, “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由此可断定,本诗的写成是在秦穆公死年,即公元前621年,是首次以文艺形式真实反映我国古代残暴杀殉制的诗篇,因而有着极为珍贵的历史认识价值和社会积极意义。
全诗共三章,以重叠复沓的形式分挽子车三良。
首句的“交交黄鸟止于棘”是起兴。 “交交”为黄雀鸣声;“棘”与下两章的“桑” “楚”,既是换韵所需,又是利用谐音使词义双关。 “棘”谐“急”,“桑”谐“丧”,“楚”指痛楚。黄雀悲鸣,急丧痛楚,为全诗渲染了哀伤气氛,与诗歌的哭悼主题、沉痛感情,在艺术上达到了和谐的一致。 “谁从穆公?”谁人要为穆公殉葬?这一句揭露性的问话,把秦穆公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正如朱熹所说:“愚按穆公于此,其罪不可逃矣。”(《诗集传》)这从葬的子车氏家三兄弟又都是怎样的人呢? “百夫之特”的“特”是匹、敌、抵得上的意思(下两章的“防”“御”同义),也就是说,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百人难敌的英才。从葬杀殉令人扼腕,而戕害艺超百人的国家栋梁,则更使人万分地痛惜愤慨。 “临其穴,惴惴其栗。”面对墓穴,血肉方刚的子车兄弟,不禁毛骨悚然、惊恐战慄。这二句诗刻画下了古代史上惨绝人寰的野蛮一幕。
诗歌的末四句,以悲愤的对天呼号和“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如可替赎,即使百个换一也甘愿的无可奈何的祈告作结,表示了对受害者的无限惋惜和深切同情。
通过对三良殉葬的歌哭,本诗揭露了暴君罪行和以人殉葬的野蛮,同时,也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大变革中,进步的人本思想的掘起和发展。
黄鸟
黄鸟黄鸟,
无集于榖,
无啄我粟。
此邦之人,
不我肯榖。
言旋言归,
复我邦族。
黄鸟黄鸟,
无集于桑,
无啄我粱。
此邦之人,
不可与明。
言旋言归,
复我诸兄。
黄鸟黄鸟,
无集于栩,
无啄我黍。
此邦之人,
不可与处。
言旋言归,
复我诸父。
黄鸟啊黄鸟! 不要停在楮树上! 不要吃我的小米! 这个国家的人们,待我没有好心肠。回去回去快回去,回到我的家乡。
黄鸟啊黄鸟! 不要停在桑树上! 不要吃我的高粱米! 这个国家的人们,没法叫他们通情理。回去回去快回去,回到我哥哥的身旁。
黄鸟啊黄鸟! 不要停在柞树上! 不要偷吃我的黍米! 这个国家的人们,不能和他们共处相来往。回去回去快回去,回到我长辈的身边。
《黄鸟》三章,章七句。关于此诗主旨,自 《传》、《笺》以来,人人说殊。《诗序》说:“刺宣王”,未明所刺者何事。毛《传》云:“宣王之末,天下室家离散,妃匹相去,有以不礼者。”郑《笺》解释说: “刺其以阴礼教亲而不至,联兄弟之不固。”即认为周宣王教民婚姻之道不够,联结兄弟不牢固。朱熹《诗集传》云“民适异国,不得其所,故作此诗。”方玉润 《诗经原始》谓:“人心浇漓,日趋愈下,有滔滔难返之势。”“刺民风偷薄也”。余冠英先生解析此诗说: “离乡背井的人在异乡遭受剥削和欺凌,更增加了对邦族的怀念。”(《诗经选》)这是对朱说的具体引申。我以为这个解说符合诗意。
诗共三章,以反复唱叹的形式,逐层深入地表达其主旨。第一章开端是: “黄鸟黄鸟,无集于榖,无啄我粟。”第二章、第三章的开头将“榖”易为 “桑”和 “栩”,将“粟”易为 “粱”和 “黍”。虽语言相似,但诗意推进了一步。榖(是楮树)、桑、栩(是柞树),在屋外,而粟、粱、黍是粮食,在屋内,从屋外到屋内,此深入一层,是层递格修辞; 接下来,第一章以 “此邦之人,不肯我榖。言旋言归,复我邦族”相续,“榖”,善。“旋”、“归”,还。第二、三章将“不我肯榖”换为 “不可与明”和 “不可与处”,将“复我邦族”换成“复我诸兄”和 “复我诸父”,“明”,同盟,信任。“处”,相处。从 “不肯我榖”到“不可与明”,再到“不可与处”,意思逐渐加重,也是层递格修辞; 从 “复我邦族” 到 “复我诸兄”,再到 “复我诸父”,亲密程度逐渐增加,仍属层递格修辞。由于成功地运用层递格修辞,使全诗“上下相接,若继踵然” (陈骙《文则》)给人以和谐完整的美感,又可使作品的内容层层紧扣,从而深化、强化了诗旨——在异乡受尽剥削和欺凌之后,对邦族和亲人的怀念。另外,诗中黄鸟出现六次,“具有三个修辞格的作用”(周振甫说,参阅四川辞书出版社《诗经楚辞鉴赏辞典》):首句“黄鸟!黄鸟!”三章相同,是复叠格;同时这是呼叫黄鸟,提出劝告,故又是呼告格;这里用的是感叹口气,所以又是感叹格。由于综合运用修辞格,此诗“其辞脱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王国维《人间词话》),令人应接不暇,美不胜收。
黄鸟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 ,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本篇是流传于春秋秦地的民歌。这是秦人的挽歌。
春秋时,秦国每以活人殉葬。周襄王三十一年(前621)秦穆公任好卒后,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其中有子车氏三兄弟。《诗序》说: “《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此说证据确凿。《左传·鲁文公六年》记载: “秦伯任好(穆公名)卒,以子车氏三子: 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史记·秦本纪》也说:“缪(通 “穆”)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 、鍼虎亦在从死之中。”本篇通过对子车氏三兄弟的哀挽,揭露了秦统治者拿活人殉葬的罪行,表达了秦人对暴君的憎恨,对子车氏兄弟悲惨命运的同情与痛惜。
本篇共分三章。首章前两句:“交交黄鸟,止于棘。”此两句言悲鸣的黄雀停息在棘树上。这是诗的起兴。二、三两章的首句与首章首句相同,第二句则换成“止于桑”、“止于楚”。桑,桑树。楚,荆树。都言黄雀停息于丛木上。“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穆公”,秦国国君,春秋五霸之一,卒于周襄王三十一年(前621),以子车氏三兄弟殉葬。“从”,指从死,即殉葬。子车是姓,奄息是名。一说,字奄,名息。此两句言,跟秦穆公殉葬的是谁?有子车氏兄弟中的奄息。二、三章的第三句与首章第三句相同,第四句则换成“子车仲行”,“子车鍼虎”。可见这种换字,有进一层指出其余二子车氏兄弟的作用。“维此奄息,百夫之特。”此言就是这个奄息,一人的才能可抵过百人。二、三章的第五、六句,则换成“维此仲行,百夫之防”;“维此鍼虎, 百夫之御”。 “百夫之防”、 百夫之特”、 “百夫之御” 皆同义。 “临其穴,惴惴其慄。”此言,奄息身临穆公的墓穴(活埋)时,恐惧战慄起来。二、三章七、八句皆同此二句。“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此言,老天爷啊!把我们的好人都杀死了。“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此言。如果能用别人代死以赎取其三人的生命,人们情愿拿一百人换回他一人。二、三章末两句皆同此二句。
秦国统治者强迫从秦穆公殉葬的子车氏三兄弟,其中每一个人的才能都可抵过百人。如此杰出的三兄弟竟被活埋于墓穴,可见秦国的统治者残暴已极。“彼苍者天!歼我良人。”秦人为之愤慨万端,仇恨满腔!“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表现秦人对三良殉葬的无限痛惜之情。
本篇三章,分别哀挽三人。每章都以树上悲鸣的黄鸟起兴,烘托出悲惨恐怖气氛,令人预感到揪心的凄凉和恐惧,从而引出子车氏兄弟而加以赞扬,然后写出殉葬时 “临其穴,惴惴其慄”的恐怖情景。最后写出诗人“彼苍者天!歼我良人”的哀号,以表达秦人对三良的切肤痛惜及对暴君的刻骨憎恨,控诉与强烈抗议。兴或兼有比义,或以作象征,或以声韵引起下文。但后者或兼有情调上的联系。如本篇三章的起兴是“交交黄鸟,止于棘”,“交交黄鸟,止于桑”,“交交黄鸟,止于楚”。这和下文 “三良”殉葬,并无意义上的联系,而是用韵脚以引起下文。但 “棘” 和 “瘠” 同音,“桑”与 “丧”同音,“楚”和 “痛楚”之 “楚”是同字,这三个字仍然能引起人们忧伤痛苦的联想。
《黄鸟》,抒情真挚激切,文笔朴素自然,是《诗经》中很有代表性的民谣,是 《诗经》 中的名篇之一。
黄鸟
此邦之人,不我肯穀③。
言旋言归④,复我邦族⑤。
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
此邦之人,不可与明⑥。
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黄鸟黄鸟,无集于栩⑦,无啄我黍。
此邦之人,不可与处。
言旋言归,复我诸父⑧。
【注释】①黄鸟:黄雀。②榖(gǔ):楮树。③穀(gǔ):善待。④旋:还。⑤复:回到。邦族:家乡,家族。⑥明:讲明。⑦栩(xǔ):柞树。⑧诸父:指各位长辈。
【鉴赏】这是弃妇之诗。
全诗三章。诗中的女子离开故乡,远嫁异国,结果遭到遗弃。她被弃之因,是因为丈夫变心,另娶新人。每章首三句写弃妇愤激之情。诗以黄鸟不要落在我的树上,不要啄食我的粮食,兴比新人不要占据我的家室,不要侵吞我的家产。这种愤激之情,与《邶风·谷风》这首弃妇诗中的“毋逝我梁,毋发我笱”颇为相似。每章中二句写丈夫之薄情。丈夫变心之后,就一反常态,再也不肯善待自己。夫妻之间本应互敬互爱,白头偕老,然而他喜新厌旧,无故将自己抛弃。像他这种人简直不可理喻,无法讲明夫妇之道。她渐渐觉得再也不能跟他生活在一起。每章末二句写弃妇决心返归。既然丈夫如此薄情,她不愿也不能这样维持下去了。于是她决心返回故乡,回到诸兄、诸父的身边去。
胡承珙《诗经后笺》说:“王氏(安石)苏氏(辙)以为贤者不得志而去;吕(祖谦)记严(粲)缉以为民适异国,不得其所之诗。”据此,诗中的主人公为贤者、流民。然而这两种说法与诗的兴象、情调不类,故不可取。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说:“黄雀就是瓦雀。这和耗子一样,也就和坐食阶级一样,没有一个国是没有的。痛恨本国的硕鼠逃了出来,逃到外国又遇着有一样的黄鸟。天地间哪里有乐土呢?倦于追求的人,他又想逃回本国了。”郭氏此说是由宋人“流民”说加以改造而成,同样不当。
黄鸟
交交黄鸟,止于棘。①谁从穆公?子车奄息。②
维此奄息,百夫之特。③临其穴,惴惴其慄。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
维此仲行,百夫之防。④临其穴,惴惴其慄。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⑤谁从穆公?子车鍼虎⑥。
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慄。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注释】 ①交交:飞而往来之貌。一说通“咬咬”,鸟鸣声。②从:从死,此指殉葬。穆公:秦穆公。子车奄息:人名,姓子车,名奄息。③特:匹敌。④防:挡,意谓一人可挡百夫。三章之“御”意同。⑤楚:荆树。⑥鍼:音qian。
【译文】 往来飞翔的黄鸟儿,落在了枣树林。是谁殉葬秦穆公?子车奄息这青年人。奄息这青年啊,是上百人才能匹敌的豪俊。当他被推近那黑沉沉的墓穴,心身恐惧战战兢兢。茫茫苍天啊太冷酷无情,你为何杀害我们的好人!假如能够赎他命,百人去死也可行! 往来飞翔的黄鸟儿,落在了桑树林。是谁殉葬秦穆公?子车仲行这青年人。仲行这青年啊,是上百人才能抵挡的精英。当他被推近那黑沉沉的墓穴,心身恐惧战战兢兢。茫茫苍天啊太冷酷无情,你为何杀害我们的好人!假如能够赎他命,百人去死也可行! 往来飞翔的黄鸟儿,落在了荆树林。是谁殉葬秦穆公?子车鍼虎这青年人。鍼虎这青年啊,是上百人才能抵御的英雄。当他被推近那黑沉沉的墓穴,心身恐惧战战兢兢。茫茫苍天啊太冷酷无情,你为何杀害我们的好人!假如能够赎他命,百人去死也可行!
【集评】 《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毛诗序》:“《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六)
汉司马迁:“缪公(穆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史记·秦本纪》)
清·牛运震:“‘谁从穆公’,呼得惨痛。钟惺所谓若为不知之词,悲之甚也。‘临穴惴惴’,写出惨状,三良不必有此状,诗人哀之,不得不如此形容尔。三良从死,何与彼苍事,怨得不近情理正妙。‘百夫之特’‘人百其身’自作映照迴绕,妙。呼应停折,缠绵淋漓。”(《诗志》)
今·陈延杰:“是篇写三良以身殉葬,真凄心伤骨。至今读之,犹觉黄鸟悲声未亏焉。《左传》言,秦收其良以死,君子知秦之不复东征,信夫!”(《诗序解》)
今·陈子展:“这是最古一篇反对以人殉葬的诗。……《墨子·节葬》篇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这应该是说的当时或和当时不远的情形。……可见当时各国诸侯还有杀殉的,并不止是秦国,不过秦国特别突出,见于记载。《左传》、《史记》载秦穆公死,殉葬的到一百七十七人之多,好像当时国人独独痛惜其中的三良,此外的一百七十四人当然是奴隶,就不足数了。同时也可想见秦国逼处西戎,文化比较落后。从秦仲以来,加速的吸收周文化,才渐渐‘与诸夏同风’,至于大量杀殉,还是奴隶社会的蛮俗罢。不过到了秦穆公时候,国人已经知道这件事不对了,《黄鸟》一诗就是一个证据。”(《国风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总案】 本诗揭露春秋时期秦国惨无人道的殉葬事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艺术情调上,牛运震、陈延杰所言“缠绵淋漓”、“凄心伤骨”可谓的评。另外,诗以黄鸟自由飞翔、栖止起兴,反衬三良之被迫从死境遇的悲惨,也显示了《诗经》民歌的高超艺术成就。
黄鸟
黄鸟黄鸟,无集于榖,无啄我粟。①此邦之人,
莫我肯谷。②言旋言归,复我邦族!③
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④此邦之人,
不可与明。⑤言旋言归,复我诸兄!⑥
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⑦此邦之人,
不可与处。⑧言旋言归,复我诸父!⑨
【注释】 ①黄鸟:黄雀。《毛传》:“黄鸟,宜集木啄杰者。”榖(gu古):楮树。粟:北方称谷子,去皮称小米。此篇主人公入赘女家,承担主要生产劳动,心爱自己的劳动成果。此处言“无集于榖,无啄我粟”,似已暗示与女家不合。②谷:善、善待,又训养。③言旋言归:回去!回去!旋、归,皆训“回”。言,句首助词。复:返、回到。邦族,邦国,族人。亦即家乡。④粱:良种之粟。一说:高粱。⑤明:即盟。信约、盟约。一说:明即弄明白、说清楚。⑥诸兄:同族兄弟。义同前章“邦族”。⑦栩(xu 许):柞树,又名栎。黍(shu 暑):即北方所说的黍子。⑧与处:共处、相处。⑨诸父:伯、叔之总称。义同前章“邦族”,亦即父母之邦。
【译文】 黄鸟听我讲一句,不要再采我的楮,莫再啄食我的粟。此邦之人无诚信,待我长工都不如。坚决离此回家走,返回我那邦国去!黄鸟听我讲一讲,不要再集我的桑,莫再啄食我的粱。此邦之人无诚善,起码信用都不讲。坚决离此回家走,寻我兄弟还家乡! 黄鸟听我讲一句,不要再集我的栩,莫再啄食我的黍。此邦之人无诚信,不可同心与同处。坚决离此回家走,回我家乡寻诸父!
【集评】 明·孙鑛:“此两篇(《白驹》《黄鸟》)与《风》无异,不知何以谓之《雅》。”(《评诗经》,《诗经直解》卷十八)
清·胡承珙:“此诗自《传》《笺》以来,人人说殊。王氏苏氏以为贤者不得志而去;《吕记》《严缉》以为民适异国,不得其所之诗。然以经文证之,此言‘复我邦族’,与《我行其野》之‘复我邦家’正同。彼明言婚姻之故’而与此诗相次,则此诗自亦为室家相弃而作。毛郑之说不可易矣。”(《毛诗后笺》十八卷)
【总案】 此为一篇弃夫诗或称弃婿诗。一个来自外地从妇而居的穷汉子(相当于后世的赘婿),在女家生活不得意,便决定“言旋言归”回到自己家乡去。此诗与下一篇《我行其野》属于姊妹篇。此篇言:“莫我肯谷”、“复我邦族”,同下篇“尔不我畜,复我邦家”同为一个意思,都是要离开妻家,返回自己家乡。《诗序》解此诗:“《黄鸟》,刺宣王也。”此话太笼统。《毛传》解释云:“宣王之末,天下室家离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礼者。”陈启源《毛诗稽古篇》进一步解释云:“《黄鸟》,《我行其野》,此二诗弃皆妇之辞也。室家相弃,由王失教而言,所以为刺也。”这一番意思是说:一,此篇为弃妇之辞;二,因宣王失教而为刺。然而,如此刺宣王,却无充分理由,一个家庭的婚事,不能统由国王去负责。至于谓为弃妇诗,此篇同《我行其野》一样,其口吻、情调等等,皆非女子之辞。《诗集传》解此诗:“东莱吕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它国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则又不若故乡焉,故思而欲归。使民如此,亦异于还定安集之时矣。今按诗文,未见其为宣王之世。”后世学者,直至当今,不少选用此说。然而这只是按诗文表面作浅解,失去了《毛传》“妃匹相去”这要点。另亦有说此咏“贤者不得志而去者”,亦仍未是。全诗三章,回环叠咏。弃夫孤闷填胸,无与置诉,皆以“黄鸟黄鸟”起兴。《毛传》系此诗: “兴也。”《诗集传》注三章为“比”,皆失之。
黄鸟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 止于楚。 谁从穆公?子车虎。 维此虎, 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诗序》说:“《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这种解说是有根据的,所以从古至今并无异议。《左传·文公六年》云“: 秦伯任好 (穆公名) 卒, 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 仲行, 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赋《黄鸟》。君子曰: 秦穆公之不为盟主也,宜哉! 死而弃民。”《史记·秦本纪》也说:“缪 (通穆) 公卒, 从死者百七十七人, 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日奄息, 仲行, 虎亦在从死之中。”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引应劭云:“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 死共此哀。”于是奄息、 仲行、 虎许诺。 及公薨, 皆从死。”秦穆公以三人殉葬的事,看来是无可质疑的。但汉代却很有两个人为之开脱,《汉书·匡衡传》载匡衡上疏称“臣窃考《国风》之诗,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郑玄的《毛诗笺》也称“三良”是“自杀以从之”,这种观点简直是闭着眼睛瞎话!
“交交黄鸟,止于棘”,这开头的两句是起兴,“交交”是黄鸟的鸣叫声,黄鸟即黄雀。“棘”是指枣树。后二章的“止于桑”、“止于楚”也都是指黄雀落在丛木上。“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这几句是说“谁跟穆公去了,是子车家的奄息,这个奄息啊,是百里挑的一个好人”。“特”是指杰出。后二章这几句句式相同,“百夫之防”之“防”是抵挡之意,即一个可以抵挡一百个。“百夫之御”的“御”也是指抵挡,与“防”相似。“临其穴,惴惴其慄”,这里“穴”指墓穴,“惴惴”是恐惧的样子,“慄”是指因恐惧而发抖。这两句翻译过来便是,“走到他的墓穴边,禁不住恐惧得发抖”。“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这四句是说“苍天啊苍天,我们的好人被夺去了生命,如果可以赎回他的性命,让我们一百个人去替他死吧”。
读此诗,我们首先可以感觉到一种压抑的,悲惨的、恐怖的气氛,这气氛有一种血淋淋的色调。“交交黄鸟,止于棘”,这里兴的运用,不仅仅是起了一个头,而且兼有写景抒情之作用。杀人殉葬的可怖的环境之中,听到几声鸟鸣,仿佛黄鸟也在为死去的人而悲鸣,让人格外感受到一种揪心的凄凉恐惧。接着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几句,叙述了良人被杀殉葬这骇人听闻的悲剧。此后“临其穴,惴惴其慄”并未直接描绘那可怖的景象,只是以亲临其境那战慄发抖的举止反衬出那是景象的恐惧和人民对于那可恶君主的痛恨,对那死去的良人的痛悼之情。“彼苍者天,歼我良人!”苍天无垠,它象征着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它又好象是人类的卫护神。自古至今,人类都对它寄予无限的敬畏与希望,无论是疾痛惨怛,还是欣喜若狂,我们常常潜意识他呼唤着苍天。在《诗经》里这样呼唤苍天的诗句有很多,都是感情剧烈之时的疾呼。《小雅·苍伯》中便有“苍天苍天! 视彼骄人,矜此劳人!”之句,在此诗中,这种呼告便是对秦君杀人殉葬的暴行的强烈控诉与抗议,这呼告是充满着激情的,所以读来格外有一种震摄力量。“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不可拒制的悲愤之情在此转化为一种真切感人的但又是无可奈何的低吟,这愿望是高尚的,富于牺牲精神的,但细细想来,它也是实在没有多少力量的。
这首《黄鸟》是出于民间,它是一首很有代表性的民谣。《诗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由神话走向诗歌的时代。《诗经》这样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文学的目光巳从那幻想的神秘莫测的上天与众神转入到现实生活的广阔天地之上,这是我国文学的第一次飞跃。《诗经》标志着我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现实主义高潮。在《诗经》中; 有劳动生产的歌,有反映战争徭役的歌,有表现爱情生活的歌,也有反剥削反压迫的歌。它接触的现实生活是如此广阔,所以象杀人殉葬这样的十分残酷的事便很自然地成为人民咏唱的题材。既然是民间歌谣,它便有朴素自然的特点。它所表现的情感是真挚激切的,没有一点点的娇揉造作。在表现方法上,除了上面分析的各章以比兴开头,意境的描绘、呼告和赋的运用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便是章节的复沓。这首诗三章十二句,各章之间仅有三处不同,“棘”、“桑”、“楚”是一处,它们都是指鸟落的丛木。“奄息”、“仲行”、“虎”是一处, 三个人都被殉葬了。“特”、“防”、“御”,三个字意义也有相似之处。可见各章的意义是有并列关系的,而从总体上看,形式是回环反复的,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咏唱,所表达的情感也如潮水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充满的哀痛之情逐渐加深,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殉葬是奴隶制下最狠毒残暴、最野蛮、最灭绝人性的制度。产生此诗的春秋时代,是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和封建制度逐渐形成的时代,于是作为奴隶制残余制度的这种人殉便受到人民的谴责。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指出,“殉葬的习俗除了秦以外,各国都是有的。不过到了这秦穆公的时侯,殉葬才成了问题。殉葬成为问题的原因,就是人的独立性的发现……人的发现,我们可以知道正是新来的时代的主要脉搏”。从郭老的话,我们是可以准确把握《黄鸟》的时代意义的。我读此诗,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有痛恨、有赞叹、有痛惜,痛恨者是君王的一具僵尸要用那么多的活人陪葬埋入泥土,这制度是多么的残忍,所赞叹者,作诗的平民百姓舍得自己的生命去换回良人,这愿望不是多么的感人,所痛惜者,那时的人民还只是在悲叹、在哀怨,而这悲叹与哀怨却是无可奈何而又无济于事的,除此而外,他们意不知所之。秦穆公死于公元前621年,直到秦末才暴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人民终于觉醒了,但这期间经过了四百年的漫长岁月,历史的发展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黄鸟
谁从穆公①?子车奄息②。
维此奄息,百夫之特③。
临其穴,惴惴其栗④。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⑤。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⑥。
交交黄鸟,止于桑。
谁从穆公,子车仲行。
维此仲行,百夫之防⑦。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身,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
谁从穆公,子车鍼虎。
维此鍼虎,百夫之御⑧。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身,人百其身。
【注释】①从:从死,殉葬。穆公:秦国国君。②子车奄息:人名。子车为姓,奄息为名。下文“子车仲行”、“子车鍼虎”同此。③特:匹敌。④惴惴(zhuì):恐惧貌。栗:战栗。⑤歼:杀害。良人:好人,善人。⑥人百其身:以一百人赎代其身。⑦防:比,相当。⑧御:义同“防”。
【鉴赏】这是控诉以人殉葬之诗。
古代有一种非常残酷的殉葬制度。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死,竟以177人陪葬,其中就包括“三良”,即子车奄息、子车仲行、子车鍼虎三兄弟。人们哀悼他们,于是就写有《黄鸟》之诗。
全诗三章。诗以黄鸟止于树上各得其所,反兴“三良”从穆公殉葬而命归黄泉,大有人命不如黄鸟之感。这“三良”乃国中之俊杰,可与“百夫”相比。“百夫之特”“百夫之防”“百夫之御”都是此意。这表现了国人对失去“三良”的无限惋惜之情。“三良”殉葬之时,下看墓穴,恐惧战栗,显得十分痛苦,使人惨不忍睹。国人亲见“三良”被活埋殉葬,悲苦无告,只好呼天抢地,疾声喊道:“老天爷啊,你为何要杀我良人?如可替换,我们愿以百人赎回他们的生命。”这表现了国人对“三良”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愤恨。
《诗序》说:“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此说有据,符合诗意。《正义》说:“是穆公命从己死,此臣自杀从之。”此说违背了诗意。诗明言“临其穴,惴惴其栗”,异常恐惧,无比痛苦,从哪里见出“三良”是心甘情愿地“自杀从之”呢?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应昭曰:“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此事的真实性姑且不论。即令属实,以人从葬仍是不道德的残酷行为。殉葬制度在春秋中叶已经开始动摇了。因此,秦穆公以“三良”等177人殉葬,乃是一种历史的反动,自然地激起了国人的不满与愤恨。
黄鸟
交交黄鸟,
止于棘。
谁从穆公?
子车奄息。
维此奄息,
百夫之特。
临其穴,
惴惴其慄。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
止于桑。
谁从穆公?
子车仲行。
维此仲行,
百夫之防。
临其穴,
惴惴其慄。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
止于楚。
谁从穆公?
子车鍼虎。
维此鍼虎,
百夫之御。
临其穴,
惴惴其慄。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小小的黄雀,落在枣树上,啾啾啾啾,不住地哀鸣。穆公死了,要用活人去殉葬。那殉葬的人是谁呢?就是子车奄息啊。提起这个奄息呀,他本是百里挑一的杰出人才,可是现在要被活埋啦! 走近那深深的坟坑,简直使人恐惧害怕得全身颤抖起来。苍天啊苍天!竟这样残酷地杀害我善良的人! 如果能够把他赎出来,我情愿死一百次去替换他。
小小的黄雀,落在桑树上,啾啾啾啾,不住地哀鸣。穆公死了,要用活人去殉葬。那殉葬的人是谁呢?就是子车仲行啊。提起这个仲行啊,他本是一百人也挡不住的能人。可是现在要被活埋啦! 走近那深深的坟坑,简直使人恐惧害怕得全身颤抖起来。苍天啊苍天! 竟这样残酷地杀害我善良的人! 如果能够把他赎出来,我情愿死一百次去替换他。
小小的黄雀,落在荆条上,啾啾啾啾,不住地哀鸣。穆公死了,要用活人去殉葬。那殉葬的人是谁呢?就是子车鍼虎啊。提起这个鍼虎呀,他本是一百人也顶不了的贤才。可是现在要被活埋啦! 走近那深深的坟坑,简直使人恐惧害怕全身颤抖起来。苍天啊苍天! 竟这样残酷地杀害我善良的人! 如果能够把他赎出来,我情愿死一百次去替换他。
《毛序》说:“《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这种说法是可信的。这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证明。郑 《笺》说:“三良,三善臣也,谓奄息、仲行、鍼虎也。” 《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史记·秦本纪》也有同样记载:“缪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对此从古至今所有论《诗》者,均无异议。
关于杀人殉葬的问题,它是一种历史现象。据考古发掘,殷商时期曾大量存在 (见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内两封郭宝钧的信)。但随着生产和社会的发展,至春秋初期,在当时中原各国,已少有所见,而且已不被社会舆论所肯定。《左传》宣公十五年,有一则关于晋国人殉事情的记载: “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 ‘必嫁是。’疾病则曰: ‘必以为殉。’ 及卒,颗嫁之,曰: ‘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很明显,魏颗认为他父亲病重时昏乱了,说的话是错误的,不予执行。这充分表现出当时人殉已被否定。魏武子与秦穆公为同时代人(关于魏武子殉葬事记于宣公十五年系追记),尽管秦地处西鄙,受戎俗影响较深,但秦晋交好,世通婚姻,应该说,人殉之俗,在当时的秦国,人们心目中一定已经是不合于道义了。它只能是奴隶制前一时代野蛮落后陋习残存的反映。《黄鸟》一诗,则正是对这一残存的野蛮落后现象的揭露和控诉。
全诗分三章,章十二句。每章开头,都以黄鸟起兴。黄鸟悲鸣着,“止于棘”、“止于桑”、“止于楚”,棘、楚皆小木,非黄雀所能安处之所; 《小雅·黄鸟》有“黄鸟黄鸟,无集于桑”,表明桑树也不是它适合停留的地方。同时就语音双关来说,棘,急也; 桑,丧也; 楚,痛楚也。所有这一切,一开始就给全诗蒙上了一层哀怨、沉痛、凄厉、悲惨的气氛。紧接着,诗人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揭示殉葬的事件。点出本诗的中心问题。秦穆公死了,要用活人去殉葬,所用的人是谁呢?是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诗人在揭露这一事件时,不满与沉痛,已经蕴藏在这一问一答之中了。第三层,诗人以无限惋惜之情追悼说,这三个人是 “百夫之特”,“百夫之防”、“百夫之御”,用百夫这个极大的数量来对比烘托出他们是难得的英雄、豪杰、贤才,而这样三位杰出人物,竟无端遭受杀害,被毁于一旦,做了毫无价值的殉葬品。罪恶的制度、罪恶的势力,毁坏了美和善,这是令人痛心的悲剧。在揭露罪恶摧毁美善的过程中,诗人不言悲、恨、痛,而其悲之切、恨之极、痛之深已深寓其中了。第四层,“临其穴,惴惴其慄”,这是写诗人的亲身感受,是对血腥残暴、阴森恐怖的殉葬场面的直接描绘,它使人不寒而栗、毛骨竦然。诗人用血淋淋的事实对惨无人道的殉葬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揭发和血泪的控诉,表达了诗人极度的悲愤和强烈的憎恨。第五层,“彼苍者天,歼我良人”,面对残酷的现实,诗人的感情再也无法控制了,火山终于爆发了。他质问苍天,要向苍天讨还血债。这是诗人反抗意识的闪光。但是,在那样沉沉的黑暗中,诗人的个人反抗,大声疾呼,又有什么用呢?最后,他无可奈何,只能提“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如果可以把三良这些人换回来,自己百死不辞,他宁愿牺牲自己,去挽救那善良的惨遭杀害的三良。他要做盗息壤的鲧,他要做东方的普罗米修斯。诗人的感情是崇高的、伟大的。
此诗语言质朴、自然而毫无修饰,所表达的感情则是沉痛、哀婉而强烈的,可以说是寓深沉于质实之中,因而读起来能震撼人心,感人肺腑。
选材典型,能抓住最激动人心的事件,提出了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因而具有强烈的揭露性和批判性,因而此诗不愧为《诗经》中现实主义的名篇。
黄鸟
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
这是一首思念故乡的诗。一位身处异乡的游子原以为来到异乡后生活处境会比家乡好些,但事与愿违,理想的破灭又使他对自己的家乡产生了思念之情,唱出了这首思乡诗。
诗的开头使用黄鸟作比喻,将异乡的那些“不我肯谷”、“莫我与明”、“不可与处”自私冷酷之人比作黄鸟。《诗经》 中用“黄鸟”处很多,《周南·葛覃》:“维叶凄凄,黄鸟于飞”。《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棘”。“黄鸟”即黄莺,也叫鹂留,仓庚。作者将异乡之人比作黄鸟是含有讽刺意义的。宋代孙奕《履斋示儿编三·黄鸟》说:“正今人稻粮熟时,黄雀群集于田垅以啄。为人所罗,所逐者,正谓此耳”。可见黄鸟是古人心目中厌恶的东西。作者用此比喻异乡之人以示其贪婪、趋利、令人讨厌。诗中的句子“无集于谷,无啄我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无集于栩,无啄我黍”非常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感情,“谷”,树名;“栩”,即柞树。诗人满怀希望地来到异乡谋生,但世态炎凉,遭人白眼,受到异乡之人的排挤和刁难,无法与他们相处,诗人心中郁积了愤懑和不平: 黄鸟啊黄鸟,不要停栖在我的楮树上,不要吃我的粮食,你们这个地方的人对待我们如此地不善良,我将回家去,回到我世代居住的邦族。本诗共分三章,每章所表现的内容是一致的,采用章节上的复沓形式但在意义上有所加深,非但“不我肯谷”而且“莫可与明”、“不可与处”,“与”,善的意思,“明”即“盟”。
在异乡生活的不幸遭遇,自然会使作者联想起在家乡时的生活情景,想起家乡的土地,想起家乡的同族叔伯和兄弟,并且在诗中“此邦”和“我邦”,“此邦之人”与“我诸兄”、“我诸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比之中表达的是对故土亲人的思念之情,抒发的是游子辗转飘零于异乡的身世之感,联想自然,对比鲜明。此诗可视为游子思乡的一段内心独白,是出于被歧视、被冷遇、被压抑下的游子发自内心的不平之音。
从此诗中游子被异乡人冷遇的事例中,可窥见当时“民风浇薄”的社会现实,这是反映西周后期至春秋社会风气日趋败坏人际关系紧张的一个侧面。
关于此诗,前人还有二种解释,一是认为此诗为刺宣王之世,民有所失者 (朱熹《诗集传》引东莱吕氏说法); 二是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认为此诗为赘婿入赘而不得。
黄鸟
诗经·秦风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若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若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若可赎兮,人百其身。
这是一首控拆以活人殉葬这一奴隶制社会的野蛮习俗的悲歌。关于秦国三良(即子车氏三位大夫——奄息、仲行、鍼虎)为穆公殉葬的事,《左传·文公六年》和《史记·秦世家》均有记载。
此诗三章叠咏。起兴两句,因黄鸟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或栖息,从反面引起联想——为什么象三良那样的好人却不得生的自由,非要替死去的穆公殉葬呢?然后六句进入正题,诗人怀着极度的惶惑和悲愤,指出三良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却要他们白白送死。既非终其天年,又非战死沙场,象牲口一样做殉葬——谁能甘心?谁不畏惧?
末四句诗人对天呼号,要求还我三良,实际上就是对野蛮的殉葬制度进行抗议。“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不仅是紧扣前文“百夫之特”、深表对三良的痛惜,而且是表示愿为埋葬这一野蛮制度而付出牺牲。好比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语极沉痛,极真诚。表现了在那个新旧制度交替的时代,秦地百姓人权意识的觉醒,是此诗的思想价值之所在。
黄鸟
一
交交黄鸟, 止于棘。
谁从穆公? 子车奄息。
维此奄息, 百夫之特。
临其穴, 惴惴其慄。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二
交交黄鸟, 止于桑。
谁从穆公? 子车仲行。
维此仲行, 百夫之防。
临其穴, 惴惴其慄。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三
交交黄鸟, 止于楚。
谁在穆公? 子车鍼虎。
维此鍼虎, 百夫之御。
临其穴, 惴惴其慄。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诗经》中同题诗有不少。如这首《黄鸟》,就有二篇:一篇是《小雅·黄鸟》,另一篇就是这首《秦风·黄鸟》。前者是记述一个寄居异国者,遭受冷遇而思归。后者,就是本诗,反映奴隶主以人殉葬的野蛮习俗,是《诗经》中比较罕见的作品。
所谓“人殉”制度,就是以活人从葬。古代奴隶主贵族死后,用很多仆人或被奴役者从葬。有的生殉(即活埋),有的杀殉。这是一个惨无人道的残酷陋习。
据《史记·秦本记》载:“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即子车)氏三人,名奄息、仲行、鍼(qián箝)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黄鸟》之诗。”这就是《秦风·黄鸟》的本事和来历。
全诗分三章,分悼三人,表现了对从葬者的痛惜,揭露了统治者的凶残无道,也反映了人民对统治者的愤怒与憎恨,以及反对残酷“人殉”制度的愿望。
* * * *
这又是一篇采用联章复迭方式写的民歌。全诗三章,每章十二句,大部分诗句相同,只在其要害处调换几个字。像这类诗,如前所说,只须精读首章,并弄清更换之词,就可全诗贯通。
下边着重解释首章词语,并顺解更换之字词。
交交:鸟鸣声。据马瑞辰《通释》云:“交交,通作咬咬,鸟声也。”这鸣声可渲染悲悼气氛,又是诗的“兴法”的运用,即以黄鸟悲鸣兴起全诗。
黄鸟:据余注《诗经选》指出,《诗经》中的“黄鸟”或指黄莺,或指黄雀,都是鸣声动听的小鸟。凡言成群飞鸣,都指黄雀,此诗也指黄雀。也有主张,不作明确肯定,由读者自己体会。
棘、桑、楚:此处的“棘”,指山枣树,或者泛指丛生灌木。桑:即以叶养蚕之桑树。楚:即荆条,一种落叶的小灌木。
穆公:即秦穆公,姓嬴,名任好。公元前621年去世,用一百多活人殉葬。子车奄息,和下文的仲行、鍼虎,均为子车氏的三个儿子,都为秦之良臣,但都在殉葬之列。
百夫之特:即百人中最杰出者;或用王力之说,“能和一百人相配的人”。因为,特,含有杰出之义,也有匹配之意。因此,可二说共存。下文的“防”与“御”,均系“抵挡”意思。即说,一百人也挡不了他。《诗集传》云:“言一人可当百夫也。”
临其穴,惴惴其慄:穴,墓穴;慄,战慄发抖。这里意思是:秦人伤悼“三良”之死,临视其穴,令人悲伤和战慄。
歼我良人:歼,尽杀,是合三人而言。句意是:尽杀好人。
人百其身;有二说:一是“一人替三良死一百次也愿意。”《郑笺》持是说。一是“拿一百人去换他一人”。朱熹作此解释。我认为,以朱说为妥。
现语译如后——这里,只译其首章,其余二章只更换几字,不译。
叽叽喳喳的黄雀,在山枣树上栖息。
谁给穆公殉葬?是子车家的奄息。
说起这个奄息啊,是位超人的干才。
走近他的墓地,令人战慄使人哀。
那苍天哟苍天,杀害好人怎一个不留?
如果准许赎他的命,愿用百人去换他一身!
* * * *
这首诗,在艺术上突出特色是复沓形式的采用。但它与前述数诗相仿,不拟多作评析。在此,我想在诗歌内容上多作些关注。
《黄鸟》在内容上,具有强烈反抗情绪和很强的暴露性。古代的殉葬制,是奴隶社会的产物,是《诗经》反映春秋时代以前社会阶级矛盾的一个重要侧面。野蛮的“人殉”,从商至周,一直到春秋后期,都在实行着。墨翟在自己的书中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墨子·节葬篇》)当孔子出生后,此种残酷制度仍在实行,因此,他起来反对它。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狠狠地咒骂了一顿。这是说:头一个造木偶(土偶)来殉葬的人,一定会绝后代的! 对于酷似人形的代制品(木俑、土俑),尚且不可,而用活人殉葬,当更要反对和痛骂了。由于秦国地处西陲,开化程度较低,“人殉”制保留得最长、最晚,直至秦穆公时(公之前659-620年),仍用国家的良臣来陪葬。因此,引起人民的强烈的不满和悲愤。这是因为这时的劳动人民,对作为人的“独立性”有了认识,故敢于对“人殉”制度提出挑战。这是主观条件。而在客观上,当时正是新生的封建制将取代腐败奴隶制的社会变革大时代。
这首诗对奴隶制的残酷野蛮本性作了深刻的揭露,“人殉”是许许多多暴行中最野蛮、最残酷的暴行。所以,诗的开头就用黄鸟悲鸣起兴,接着,高度评赞“三良”,再接着指出了殉葬制的悲剧;最后,忍不住以极度悲愤的心情,反复质问苍天:为什么尽是毁灭我们的好人,这是谁的罪过?并提出:愿用百人之躯去赎一位“良人”! 这不要误解诗人的用意,不是说人民在向统治者求情、妥协,而正好相反,是揭露“人殉”者的罪大恶极,要葬送那么多活生生的性命!
因此说,这首诗的反抗意识十分鲜明,揭露也非凡深刻,对奴隶制度的本性的刻划也很入木,确是一首难得的古代佳作。
黄鸟
[原文]
交交黄鸟,
止于棘。
谁从穆公?
子车奄息。
维此奄息,
百夫之特。
临其穴,
惴惴其慄。(鲁慄作栗。)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鲁兮作也。)
人百其身。
(棘、息、特,之部。穴、慄,脂部。天、人、身,真部。)
交交黄鸟,
止于桑。
谁从穆公?
子车仲行。
维此仲行,
百夫之防。
临其穴,
惴惴其慄。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桑、行、防,阳部。穴、慄,脂部、天、人、身,真部。)
交交黄鸟,
止于楚。
谁从穆公?
子车鍼虎。
维此鍼虎,
百夫之御。
临其穴,
惴惴其慄。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楚、虎、御,鱼部。穴、慄,脂部;天、人、身,真部。)
[译文]
小小的黄雀,落在枣树上,啾啾啾啾,不住地哀鸣。穆公死了,要用活人去殉葬。那殉葬的人是谁呢?就是子车奄息啊。提起这个奄息呀,他本是百里挑一的杰出人才,可是现在要被活埋啦! 走近那深深的坟坑,简直使人恐惧害怕得全身颤抖起来。苍天啊苍天!竟这样残酷地杀害我善良的人! 如果能够把他赎出来,我情愿死一百次去替换他。
小小的黄雀,落在桑树上,啾啾啾啾,不住地哀鸣。穆公死了,要用活人去殉葬。那殉葬的人是谁呢?就是子车仲行啊。提起这个仲行啊,他本是一百人也挡不住的能人。可是现在要被活埋啦! 走近那深深的坟坑,简直使人恐惧害怕得全身颤抖起来。苍天啊苍天! 竟这样残酷地杀害我善良的人! 如果能够把他赎出来,我情愿死一百次去替换他。
小小的黄雀,落在荆条上,啾啾啾啾,不住地哀鸣。穆公死了,要用活人去殉葬。那殉葬的人是谁呢?就是子车鍼虎啊。提起这个鍼虎呀,他本是一百人也顶不了的贤才。可是现在要被活埋啦! 走近那深深的坟坑,简直使人恐惧害怕全身颤抖起来。苍天啊苍天! 竟这样残酷地杀害我善良的人! 如果能够把他赎出来,我情愿死一百次去替换他。
[评介]
《毛序》说:“《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这种说法是可信的。这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证明。郑 《笺》说:“三良,三善臣也,谓奄息、仲行、鍼虎也。” 《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史记·秦本纪》也有同样记载:“缪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对此从古至今所有论《诗》者,均无异议。
关于杀人殉葬的问题,它是一种历史现象。据考古发掘,殷商时期曾大量存在 (见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内两封郭宝钧的信)。但随着生产和社会的发展,至春秋初期,在当时中原各国,已少有所见,而且已不被社会舆论所肯定。《左传》宣公十五年,有一则关于晋国人殉事情的记载: “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 ‘必嫁是。’疾病则曰: ‘必以为殉。’ 及卒,颗嫁之,曰: ‘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很明显,魏颗认为他父亲病重时昏乱了,说的话是错误的,不予执行。这充分表现出当时人殉已被否定。魏武子与秦穆公为同时代人(关于魏武子殉葬事记于宣公十五年系追记),尽管秦地处西鄙,受戎俗影响较深,但秦晋交好,世通婚姻,应该说,人殉之俗,在当时的秦国,人们心目中一定已经是不合于道义了。它只能是奴隶制前一时代野蛮落后陋习残存的反映。《黄鸟》一诗,则正是对这一残存的野蛮落后现象的揭露和控诉。
全诗分三章,章十二句。每章开头,都以黄鸟起兴。黄鸟悲鸣着,“止于棘”、“止于桑”、“止于楚”,棘、楚皆小木,非黄雀所能安处之所; 《小雅·黄鸟》有“黄鸟黄鸟,无集于桑”,表明桑树也不是它适合停留的地方。同时就语音双关来说,棘,急也; 桑,丧也; 楚,痛楚也。所有这一切,一开始就给全诗蒙上了一层哀怨、沉痛、凄厉、悲惨的气氛。紧接着,诗人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揭示殉葬的事件。点出本诗的中心问题。秦穆公死了,要用活人去殉葬,所用的人是谁呢?是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诗人在揭露这一事件时,不满与沉痛,已经蕴藏在这一问一答之中了。第三层,诗人以无限惋惜之情追悼说,这三个人是 “百夫之特”,“百夫之防”、“百夫之御”,用百夫这个极大的数量来对比烘托出他们是难得的英雄、豪杰、贤才,而这样三位杰出人物,竟无端遭受杀害,被毁于一旦,做了毫无价值的殉葬品。罪恶的制度、罪恶的势力,毁坏了美和善,这是令人痛心的悲剧。在揭露罪恶摧毁美善的过程中,诗人不言悲、恨、痛,而其悲之切、恨之极、痛之深已深寓其中了。第四层,“临其穴,惴惴其慄”,这是写诗人的亲身感受,是对血腥残暴、阴森恐怖的殉葬场面的直接描绘,它使人不寒而栗、毛骨竦然。诗人用血淋淋的事实对惨无人道的殉葬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揭发和血泪的控诉,表达了诗人极度的悲愤和强烈的憎恨。第五层,“彼苍者天,歼我良人”,面对残酷的现实,诗人的感情再也无法控制了,火山终于爆发了。他质问苍天,要向苍天讨还血债。这是诗人反抗意识的闪光。但是,在那样沉沉的黑暗中,诗人的个人反抗,大声疾呼,又有什么用呢?最后,他无可奈何,只能提“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如果可以把三良这些人换回来,自己百死不辞,他宁愿牺牲自己,去挽救那善良的惨遭杀害的三良。他要做盗息壤的鲧,他要做东方的普罗米修斯。诗人的感情是崇高的、伟大的。
此诗语言质朴、自然而毫无修饰,所表达的感情则是沉痛、哀婉而强烈的,可以说是寓深沉于质实之中,因而读起来能震撼人心,感人肺腑。
选材典型,能抓住最激动人心的事件,提出了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因而具有强烈的揭露性和批判性,因而此诗不愧为《诗经》中现实主义的名篇。
黄鸟
〔原文〕
黄鸟黄鸟,
无集于榖,
无啄我粟。
此邦之人,
不我肯榖。
言旋言归,
复我邦族。
(榖、粟、榖、族,侯部。)
黄鸟黄鸟,
无集于桑,
无啄我粱。
此邦之人,
不可与明。
言旋言归,
复我诸兄。
(桑、粱、明、兄,阳部。)
黄鸟黄鸟,
无集于栩,
无啄我黍。
此邦之人,
不可与处。
言旋言归,
复我诸父。
(栩、黍、处、父,鱼部。)
〔译文〕
黄鸟啊黄鸟! 不要停在楮树上! 不要吃我的小米! 这个国家的人们,待我没有好心肠。回去回去快回去,回到我的家乡。
黄鸟啊黄鸟! 不要停在桑树上! 不要吃我的高粱米! 这个国家的人们,没法叫他们通情理。回去回去快回去,回到我哥哥的身旁。
黄鸟啊黄鸟! 不要停在柞树上! 不要偷吃我的黍米! 这个国家的人们,不能和他们共处相来往。回去回去快回去,回到我长辈的身边。
〔评介〕
《黄鸟》三章,章七句。关于此诗主旨,自 《传》、《笺》以来,人人说殊。《诗序》说:“刺宣王”,未明所刺者何事。毛《传》云:“宣王之末,天下室家离散,妃匹相去,有以不礼者。”郑《笺》解释说: “刺其以阴礼教亲而不至,联兄弟之不固。”即认为周宣王教民婚姻之道不够,联结兄弟不牢固。朱熹《诗集传》云“民适异国,不得其所,故作此诗。”方玉润 《诗经原始》谓:“人心浇漓,日趋愈下,有滔滔难返之势。”“刺民风偷薄也”。余冠英先生解析此诗说: “离乡背井的人在异乡遭受剥削和欺凌,更增加了对邦族的怀念。”(《诗经选》)这是对朱说的具体引申。我以为这个解说符合诗意。
诗共三章,以反复唱叹的形式,逐层深入地表达其主旨。第一章开端是: “黄鸟黄鸟,无集于榖,无啄我粟。”第二章、第三章的开头将“榖”易为 “桑”和 “栩”,将“粟”易为 “粱”和 “黍”。虽语言相似,但诗意推进了一步。榖(是楮树)、桑、栩(是柞树),在屋外,而粟、粱、黍是粮食,在屋内,从屋外到屋内,此深入一层,是层递格修辞; 接下来,第一章以 “此邦之人,不肯我榖。言旋言归,复我邦族”相续,“榖”,善。“旋”、“归”,还。第二、三章将“不我肯榖”换为 “不可与明”和 “不可与处”,将“复我邦族”换成“复我诸兄”和 “复我诸父”,“明”,同盟,信任。“处”,相处。从 “不肯我榖”到“不可与明”,再到“不可与处”,意思逐渐加重,也是层递格修辞; 从 “复我邦族” 到 “复我诸兄”,再到 “复我诸父”,亲密程度逐渐增加,仍属层递格修辞。由于成功地运用层递格修辞,使全诗“上下相接,若继踵然” (陈骙《文则》)给人以和谐完整的美感,又可使作品的内容层层紧扣,从而深化、强化了诗旨——在异乡受尽剥削和欺凌之后,对邦族和亲人的怀念。另外,诗中黄鸟出现六次,“具有三个修辞格的作用”(周振甫说,参阅四川辞书出版社《诗经楚辞鉴赏辞典》):首句“黄鸟!黄鸟!”三章相同,是复叠格;同时这是呼叫黄鸟,提出劝告,故又是呼告格;这里用的是感叹口气,所以又是感叹格。由于综合运用修辞格,此诗“其辞脱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王国维《人间词话》),令人应接不暇,美不胜收。
黄鸟huángniǎo

黄雀。《周南·葛覃》一章:“维叶萋萋,黄鸟于飞。”毛《传》:萋萋,茂盛貌。黄鸟,抟黍也。” 《尔雅·释鸟》:“皇,黄鸟。”郝懿行《义疏》:“按此即今之黄雀,其形如雀而黄,故名黄鸟,又名抟黍。”王先谦《集疏》:“段玉裁、焦循遂谓毛《传》以‘抟黍’ 释 ‘黄鸟’,不云即 ‘仓庚’,是诗之‘仓庚’为‘黄莺’,而‘黄鸟’为今之‘黄雀’。黄雀啄粟,故有 ‘抟黍’ 之名,因改抟为‘搏’以成其义。”《秦风·黄鸟》一章: “交交黄鸟,止于棘。” 毛《传》: “交交,小貌。”棘,小木。《小雅·绵蛮》一章。“绵蛮黄鸟,止于丘阿。”毛《传》:“绵蛮,小鸟貌。丘阿,曲阿也。”《本草纲目》李时珍〔释名〕: “雀,小而黄口者为黄雀。”〔集解〕: “雀,处处有之。羽毛斑褐,颔嘴皆黑。头如颗蒜,目如擘椒。尾长二寸许,爪距黄白色,跃而不步。其视惊瞿,其目夜盲,其卵有斑,其性最淫。小者名黄雀。八九月群飞田间。体绝肥,背有脂如披绵。”一说,黄莺。《邶风·凯风》四章:“𪿐睆黄鸟,载好其音。”毛《传》: “𪿐睆, 好貌。”《本草纲目》李时珍〔释名〕:“莺,黄鸟、离黄、仓庚。”〔集解〕:“莺处处有之。大于鸜鹆,雌雄双飞,体毛黄色,羽及尾有黑相间,黑眉尖嘴,青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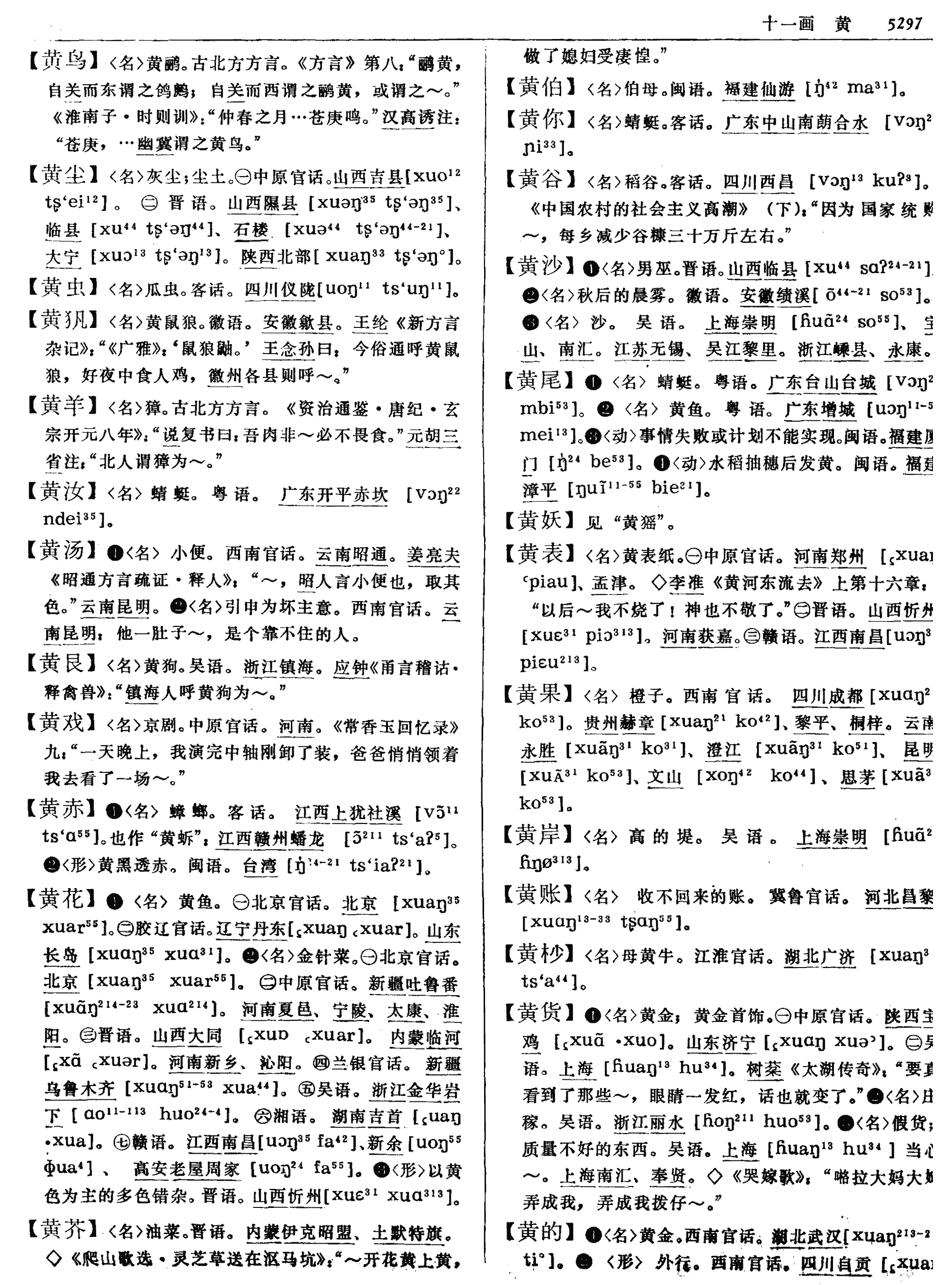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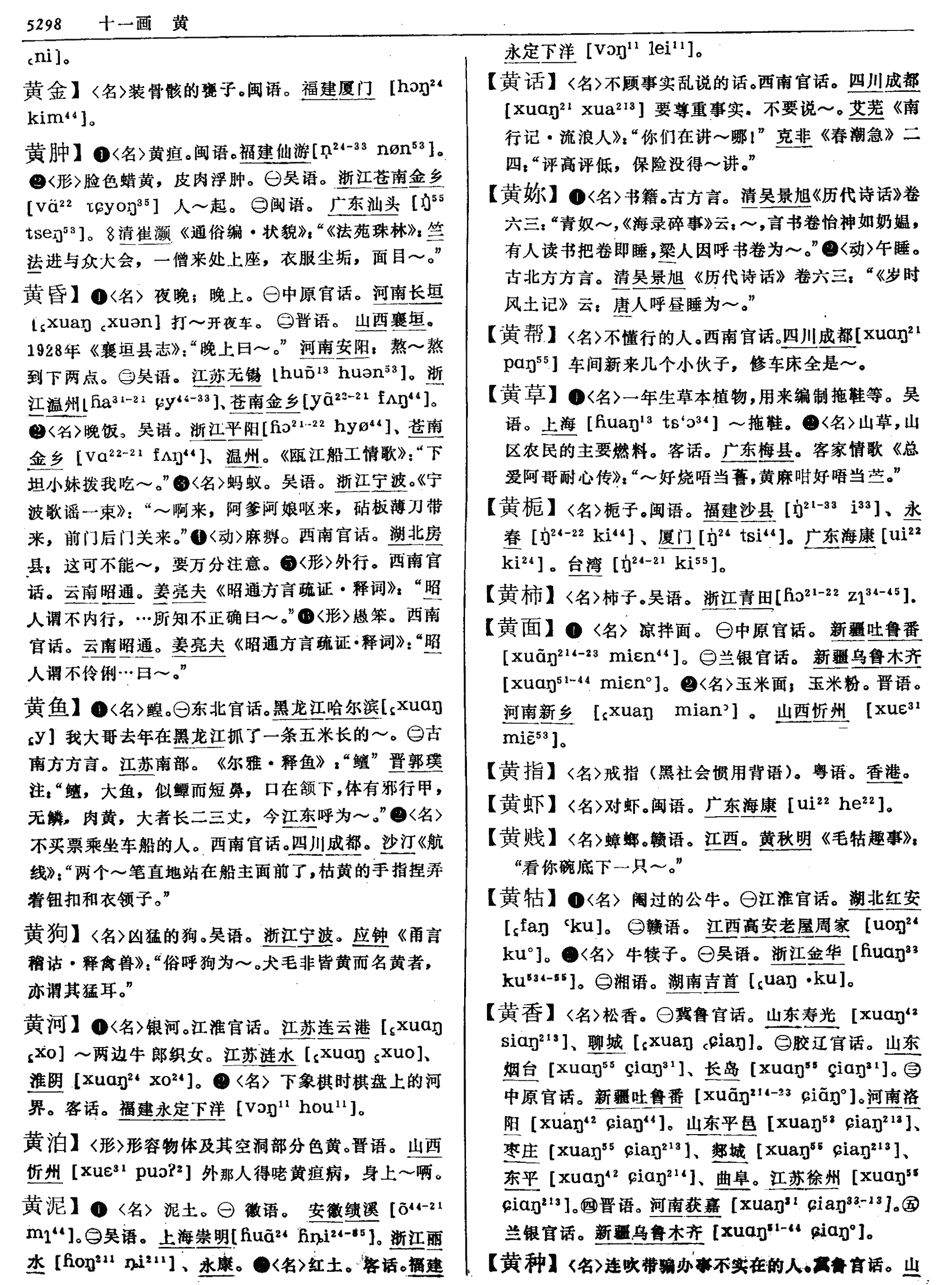
黄鸟
鸟名。神话传说,司食尘,玄蛇之鸟。《山海经·大荒南经》:“黑水之南,有玄蛇、食尘。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郭璞注“天帝神仙药在此也。”黄鸟司食尘,玄蛇,盖惧其窃食天帝神仙药也。
即黄鸝。《詩·周南·葛覃》:“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鄭玄箋:“黄鳥,搏黍也。”孔穎達疏引陸機云:“黄鳥,黄鸝留也,或謂之黄栗留,幽州人謂之黄鸎。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黄,一名楚雀。”按,黄雀亦得稱黄鳥,實不同于黄鸝。二者異物同名。參見本類“黄雀”。
观赏鸟
眉画型的小鸟:鹪(鹪鹌) 巧雀 巧妇(巧妇鸟) 巧女 蔑雀 袜雀 桃雀 桃虫 桑串 蔑爵 蒙鸠 工爵 工雀 女匠 宁鳺 布母 桑飞 鸱鸮 黄脰雀
黄鹂:鹂(鹂黄) 莺(莺鸟;莺儿;莺翁;莺鹂;黄莺;柳莺;流莺;夜~;春~) 皇 黄公 黄鸟 黄袍 黄离(黄离留) 离黄 黧黄黎黄 鵹黄 丽黄 楚雀 栗留(黄栗留) 云鸧 鸧鹒 仓庚抟黍 树串 长股 鷅鹠 黄伯劳水鸦儿 金衣公子
小莺:莺雏 莺儿
鹦鹉:鹦(鹦歌;鹦哥;鹦母) 辩哥 翠哥 莺哥 陇客 陇禽 陇鸟 干皋 干睪 婴武 婴母 臊陀 慧鸟 聪明鸟 能言鸟 南越鸟 绿衣使者
白鹦鹉:雪女 雪衣(雪衣女;雪衣娘)
八哥鸟:鹆(鸲鹆;鸜鹆) 寒皋 八哥
孔雀:孔(孔鸟;孔爵) 越鸟 越禽 金尾 南客 鸾凤友
鸳鸯:鸳(鸳鸟;文鸳) 鸯 匹鸟 疋鸟 并禽 黄鸭 韩凭 韩冯 韩朋 节木鸟 河曲鸟
各种鸟名
鸡(秧~;珠~;春~;褐~)皇 鸢 凫 鸠(~妇;此鸟 ~;斑~;绿~;南~;睢~;鹃~;鵽~;鸤~;鹁~) 鸨 鹝![]() 鸫(乌~) 鸲(歌~;红尾~) 鸻 鹀 鴓 鴡(~鸠) 鴃鴔 鹨(树~;水~;天~) 鹳 鹬 鹯 鹑 鸀 鹲 鹘(~鸼;~鸠) 鹱 鷽 隼(小~;燕~)鹛 鷁 鹟 鹎 鹁 鶡 鹇(~客) 鸸 雒
鸫(乌~) 鸲(歌~;红尾~) 鸻 鹀 鴓 鴡(~鸠) 鴃鴔 鹨(树~;水~;天~) 鹳 鹬 鹯 鹑 鸀 鹲 鹘(~鸼;~鸠) 鹱 鷽 隼(小~;燕~)鹛 鷁 鹟 鹎 鹁 鶡 鹇(~客) 鸸 雒 ![]() (
(![]() 雀) 鹣(云鹣) 鵽(鵽鸠;鵽雀;霜~) 鸬(鸬鹚) 山鹊 天鸬 百灵 百舌博劳 虫蚁 虫鷖 蚁裂 郭公 娇凤 题凤 晖目 勃姑 雅乌 箴疵 企鹅 鹩哥 风鸟 河鸟 文鸟 孝鸟 琴鸟 犀鸟 椋鸟(欧~) 翁鸟 雷鸟 蜂鸟 榛鸟鷛鸟 鸸鹋 ?鹡 鸺鹠 鸜鹆鹪鹩 ?鷉 鸋鴂 鸑鷟 鹁鸪 鹧鸪 鹌鹑 鹪鹏 白头翁 吊鱼郎秦吉了 太阳鸟 太平鸟 火烈鸟比翼鸟 巧妇鸟 极乐鸟 告春鸟芙蓉鸟 园丁鸟 绣眼鸟 啄花鸟带寿鸟 绣眼眼
雀) 鹣(云鹣) 鵽(鵽鸠;鵽雀;霜~) 鸬(鸬鹚) 山鹊 天鸬 百灵 百舌博劳 虫蚁 虫鷖 蚁裂 郭公 娇凤 题凤 晖目 勃姑 雅乌 箴疵 企鹅 鹩哥 风鸟 河鸟 文鸟 孝鸟 琴鸟 犀鸟 椋鸟(欧~) 翁鸟 雷鸟 蜂鸟 榛鸟鷛鸟 鸸鹋 ?鹡 鸺鹠 鸜鹆鹪鹩 ?鷉 鸋鴂 鸑鷟 鹁鸪 鹧鸪 鹌鹑 鹪鹏 白头翁 吊鱼郎秦吉了 太阳鸟 太平鸟 火烈鸟比翼鸟 巧妇鸟 极乐鸟 告春鸟芙蓉鸟 园丁鸟 绣眼鸟 啄花鸟带寿鸟 绣眼眼
云雀:天鹨 告天子
信天翁:信天公 信天缘
相思鸟:相思(相思子) 游香
伯劳:鴂(题鴂) 鴃 博劳 伯鹩 伯赵 百鹌
鹡鸰:鸰 钱母 连钱 石鸟 雪姑 脊令 精列 连点七 九颠迁
斑鸠:锦鸠 鹁鸠 祝鸠 斑隹 鷽鸠
黄雀:黄鸟 王母(王母使者) 臛皇
白鹇:鹇 闲客 卓雉 白翰 白雉 素雉 玄素先生
鹧鸪:越雉 怀南 南禽 越禽 逐影 逐隐 内史 花豸 首南鸟
鸩鸟:昙(~鸟) 云鸟 运日 云日 云白 顷刻虫 一拂鸟 同力鸟
鸵鸟:大雀 大爵 马爵 驼鸡 驼蹄鸡骨托禽
戴胜:戴南 戴任 戴纴 鶠鸠 鸱鸠 山和尚
鹈鹕:鹈 鴺胡 鵹鹕 塘鹅 淘河(淘河鸟) 淘鹅 驼鹅 驼鹤 汙泽洿泽 犁塗 犁鹕
秃鹙:鹙(秃鹙) 秃秋 扶老 延居 乘风
黄鸟huáng niǎo
❶黄莺。《诗·周南·葛覃》“~~于飞,集于灌木。”
❷指黄雀。《诗·秦风·黄鸟》:“交交~~,止于棘。”
黄鸟
《诗经·秦风》中的一篇。《春秋左传·文公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任好为秦穆公之名,卒于周襄王三十一年(前621),以177人殉葬。全诗三章: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 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 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诗中虽未否定殉葬制度,却对受害者给予极大同情。
黄鸟
《诗经·秦风》中的一篇。《春秋左传·文公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任好为秦穆公之名,卒于周襄王三十一年(前621),以177人殉葬。全诗三章: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 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 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诗中虽未否定殉葬制度,却对受害者给予极大同情。
黄鸟
即《诗·小雅·黄鸟》。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康公杀177人为之殉葬。其中有子车兄弟三人。秦人作是诗刺秦君暴行并哀悼子车兄弟。
- 高举人现丑是什么意思
- 高举双臂是什么意思
- 高举奋飞是什么意思
- 高举拳头轻轻放是什么意思
- 高举拳头轻轻放——手下留情是什么意思
- 高举摩太清,永绝矰缴惧。是什么意思
- 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前进是什么意思
- 高举深藏是什么意思
- 高举的样子是什么意思
- 高举红旗是什么意思
- 高举腿坐转体180°是什么意思
- 高举腿支撑是什么意思
- 高举远去是什么意思
- 高举远引是什么意思
- 高举远蹈是什么意思
- 高举阁是什么意思
- 高举,高高翘起是什么意思
- 高乃依是什么意思
- 高乃濟是什么意思
- 高义是什么意思
- 高义云天是什么意思
- 高义今则无 舒位 沈青斋是什么意思
- 高义盛是什么意思
- 高义薄云是什么意思
- 高义薄云天是什么意思
- 高乌甲素是什么意思
- 高乎儿的是什么意思
- 高乐是什么意思
- 高乐福是什么意思
- 高乐(法)是什么意思
- 高乔人是什么意思
- 高也是什么意思
- 高也平是什么意思
- 高也有限是什么意思
- 高书勋是什么意思
- 高买是什么意思
- 高乳糜微粒血症是什么意思
- 高乾是什么意思
- 高乾和是什么意思
- 高乾杀孙百鸡举事是什么意思
- 高乾赐死案是什么意思
- 高了是什么意思
- 高二是什么意思
- 高二氧化碳处理是什么意思
- 高二适是什么意思
- 高二适草书湘娥诗是什么意思
- 高二適是什么意思
- 高二鲍是什么意思
- 高于是什么意思
- 高于岑楼是什么意思
- 高于正常的温度是什么意思
- 高于流俗是什么意思
- 高于票面价格是什么意思
- 高亏是什么意思
- 高云是什么意思
- 高云从是什么意思
- 高云台是什么意思
- 高云和是什么意思
- 高云堂是什么意思
- 高云堂诗集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