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句
又称“绝诗”、“截句”、“断句”。近体诗之一种。绝、截、断均含短截之义,或谓其截取律诗而成,故名。以四句二韵为定格,平仄、押韵格式与律诗同,惟不拘求对仗,以首句入韵较为常见。亦有五言、七言二体,每句五言者为五绝,每句七言者为七绝。唐以前绝句多只讲押韵,不究平仄,为区别于近体绝句,称为“古绝”。
绝句
地炉无火一囊空,雪似杨花落岁穷。
乞得苎麻缝破衲,不知身在寂寥中。
《五灯会元》卷三记载着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唐法常禅师偏居大梅山中,时有一僧于山中采杖迷路而至其草庵。那僧人见庵主端坐默念,似浑然超脱于身外世界,奇而问之:“和尚在此多少时?”法常禅师答道:“只见四山青又黄。”僧人无心契,急于离山归去,又问:“出山路向什么处去?”禅师淡然答:“随流去。”那僧人无悟而返……这段对话看似平常,其实寓意是颇深的。僧人的问话与禅师的回答所包蕴的丰富内涵正是对“禅”的生活追求的朴素昭示。“随流去”,实在是深含玄理的禅悟妙语。从实际角度看,人烟聚集之地总是与水相连相近的,那么“随山间流水而去” 自然便踏上了归途。而若从“禅”的角度看,则暗示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生活本应像无争自流的流水那样自然而然,无所欲亦无所忧,不为任何的外在所困扰,如此才能把握于人生长河中航行的正确方向。只有在这自然而然的生活流程中,才能超度真正的人生彼岸,获得真实与绝对自由的人生体验。这就是禅的追求,禅的境界,禅的生命的展现。于是,任何的外在都于这至高无上的人生境界中失去了其世俗意义,山居而不孤寂,草庵亦非清苦; 神交天地,优游万象,佛我归一,自在自适; 一切 “业障” 自然泯除,一切 “苦谛” 自然消释,唯余“涅槃”后的 “再生”,“拈花”时的 “微笑” 了——生命由此而大放异彩!
九百多年前的重喜长老便深深悟入了如此美妙的人生境界。那是一个岁余清寒的夜晚,窗外雪花飘飞,室内地炉 (用于生火取暖,又可煮茶或温酒的炉灶。唐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诗句:“暖屋绣帘红地炉。”又宋陈与义《招张仲宗》诗句:“幽子朝朝只地炉。”翁森《四时读书乐》诗句:“地炉茶鼎烹活火。”)无火,一件衲衣也已破敝不堪,甚至要用苎麻补缀。然而,正如豪奢的物质生活未必带来生之真乐一样,贫困的物质生活也未必会抹杀生之真乐,它带给重喜长老的并非寂灭寥落的伤悲与凄苦,相反,于此无忧无碍、净心涤虑的生活境况中,长老早已超然物外,把自己融于那种“随流去”的生命体验之中了,就像“山中无日历,寒尽不知年” (唐太上隐者 《答人》) 的法常禅师一样 “不知身在寂寥”中。
重喜这一“七绝”,其实倒是一则偈颂,诗味不足而禅理颇深。以诗观之,唯 “雪似杨花落岁穷”一句耳。然以杨花喻雪实不稀奇,如约比重喜稍前或与之同时的诗人梅尧臣有诗句:“杨花扑扑白漫地” ( 《次韵和刁景纯春雪戏意》)、词家苏东坡有词句: “飞雪似杨花” (《少年游》) 等等。若以禅观之,则悟性即见、满篇玄机。《宋诗纪事》所载这一“绝句”是从周紫芝《竹坡诗话》辑入的,与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载稍有出入,(“地炉无火客囊空,雪似杨花落岁穷。拾得断麻缝坏衲,不知身在寂寥中。”) 但与旨意无碍。佛与禅讲“身空”(佛家也称身为“皮囊”)、“心空”,亦可谓“无欲”、“无扰”,因 “空”而“净”,因 “空”而“明”,因“空”而“见性见佛”,这是修行的法门。其实,著名的神秀偈与慧能偈——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佛性本清净,何处惹尘埃”,都是说明这样的道理,只是对“空”的认识程度与“见性见佛”的过程上有所差别而分 “渐悟”与 “顿悟”罢了。由此看来,“地炉无火一囊空,”正是“身空”、“心空”的形象化喻指。这也可说是禅的第一境界。
“雪似杨花落岁穷。”同样,如果从禅的角度看,那么这里的“杨花”与“雪”也不能简单地视作因二者形象上的相似而作的文学化比喻。“禅”讲“无分别心”,否定相对的价值观念,所以马祖道一见到刚刚飞过的野鸭却说明明还在,所以善慧菩萨说“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那么,说重喜长老于那清寒的雪花中看到的是盎然春意,亦或说是把那岁余飘飞的雪花看作了春日飞舞的杨花,就不足为怪了。其实,“雪似杨花落岁穷”,不也正是“雪与春归落岁前” (梅尧臣《次韵和刁景纯春雪戏意》) 之意吗? 只是在 “禅”的眼里,雪花与杨花、冬与春,同在一 “道”(自然),已根本无分别在了。这才是绝对的永恒的真实,就像法常禅师以 “只见四山青又黄”否定岁律推移变迁的相对时间观念一样。由 “空”而 “明”,由不执着外在而洞见 “大道”,此可谓禅的第二境界。
寒冷的冬雪与温煦的春日同在,同样,贫乏的物质生活也无碍真实尊贵的生命体悟。当我与佛与道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的时候,则如庄生化蝶、列子御风、老子在道犹龙,获得了绝对的精神自由与真实的生命永恒及自然而然、自在自适的生活愉悦。这就是重喜长老在那清幽静谧的寒夜,冥冥然“不知身在寂寥中”的精神境界,也是禅的至高无上的感悟境界。《宋诗纪事》另从《老学庵笔记》辑载重喜两句“诗”:“行到寺中寺,坐观山外山。”也只能作如是观: 修行到内在精神体验的最高境界,而优游超然地返观象外。不能不说重喜长老是深悟玄机的得道高僧。难怪陆游称其这一“七绝”为“警句”,周紫芝也叹道:“此岂捕鱼者之所能哉? 解悟如此,盖得观音智慧力也。”
禅并不看重任何的外在和世俗价值,禅僧们往往安于清贫朴素的生活。前面提到的那位山中问路的僧人依其师意又去招请法常禅师时,法常禅师作了这样一偈:“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遇之犹不顾,郢人哪得苦追寻。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他拒绝了僧人的邀请,同时也避弃了世俗生活。重喜长老也一样,无视物质生活的窘况而安贫自适。但是,不能不明确这样的认识: 神所追求的是更为深沉内在的精神光明,而并非清贫生活本身。禅以为,世俗生活的 “所有欲”最易诱使生活走向不幸的岐途,也是悟入禅境的极大限制与障碍。可知,禅僧们自甘清贫的生活只是为了把这种限制与障碍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而已。其实,禅,尤其是被认为最能体现中国禅实质的 “南禅”,更讲禅悟的 “日常性”,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秉承于原始佛教的种种清规戒律。无论身处何境,都不失禅的无限意蕴,都可感悟禅的非凡魅力,所谓劈柴担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在道场,把那种“随流去”的生活原则发挥得更自然朴实,更彻底明确,也使“参禅”更具生活的积极意义。我们在领悟重喜的这则偈颂时,应有这样的认识。当然,悟禅者各有己见。
绝句
向来松桧喜无恙,坐久复闻南涧钟。
隐隐修廊人语绝,四山滴沥雪鸣风。
这是一首纪游诗。诗人旧地重游,所以四周景物都很熟悉,因而也倍感亲切。在写法上,将时间的推移、空间的变换与内心意绪的变化顺理成章地融合在一起,显得特别精巧。
诗分两层。前两句写入山路上之所见与所闻:“向来松桧喜无恙,坐久复闻南涧钟。”“向来”即旧时,“桧”即桧柏,“无恙”指没有受到损伤。诗人进得山来,看到山路两旁旧时的松柏依然如昨,不由十分高兴。大概是因为久别重逢而倍觉亲切吧,诗人竟坐下来不肯走了,他或许是在尽情观赏,或许是想和它们畅叙衷曲? 当南涧中旧时禅院里又一次撞响那悠悠钟声,诗人才突然醒悟: 自己在这里盘垣得太久了。“南涧”,山南侧的涧谷。《诗经·国风·采萃》: “于以采萃,南涧之滨。”这里指山中禅院的处所。循着这缥缈的钟声,诗人寻得了旧时的禅院,后两句便写步入禅院后所见的景物与感受: “隐隐修廊人语绝,四山滴沥雪鸣风。”“隐隐”,隐约不分明。张旭《桃花溪》: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滴沥”:稀疏的水滴声,此处借指风雪声。在山寺的长廊上,游人稀少,人们的说话声依稀隐约,似有若无,最终归于一片静谧之中。正由于静到极点,诗人才对山寺四周崇山峻岭中那搅天风雪、水瘦山寒的环境气氛,有着特别强烈的感受,以至连山中冰雪落地的声音也能清晰地分辨出来。他顿觉置身于一个寥廓空寂的禅悦之境里。首句的一个“喜”字,透露出诗人步入禅院、重悟禅趣的怡悦之情。
这首诗用字也极精确。因为是重游,而且是写进山乃至入寺之所历,景物就有今昔与前后的特点,但在诗人的感觉中,有的景物并无太大变化,于是只用 “向来”、“复闻”数字,便前勾后联,用一副笔墨将其特征尽数写出,显得特别经济。在结构上这首诗也颇精巧,那漫天风雪,诗人在入山路上其实就已领略了,但为了突现旧地重游的喜悦,诗人在头两句中有意不说出,直到全诗末尾才点明,这就将景物的描写和心绪的变化有机地结合了在一起,既自然而又精炼。
绝句
春朝湖上风兼雨,世事如花落又开。
退省闭门真乐处,闲云终日去还来。
这首七绝原载 《海盐图经》。
从首句“春朝湖上风兼雨”所写春朝、湖上、风、雨看,似是写景,然与下边三句所写内容联系起来分析,当是以比兴手法引出诗中所写的人间事理。诗写的是春天,正是花开的季节,而由于风吹雨打,花开花落是很自然的事。诗人在此用花开花落来喻世事之无常迁流。佛教认为“诸行无常”,即一切事物有生必有死,不能保持其永久的生命。一切宗教都追求永恒的存在,佛教也不例外。那么,如何在无常迁流的世界中追求永恒呢?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生于这个世界,跳出这个世界。这就是佛教所说的涅槃解脱。
“退省闭门真乐处”句,是写正觉掩门修道的情趣与感受。“退省”,指按禅宗“内悟自心”的方式去悟禅;“闭门”指远离尘世之一切喧嚣烦恼。故曰 “真乐处”。
“闲云终日去还来”,表面看是写正觉常见的自然景象,实则是她入禅为尼之后的心理写照。禅宗常用 “白云”喻任运自然的修行生活。佛徒主张排除世间一切欲望,努力自悟本性。自悟了本性之后,要时时注意保持它,“莫失莫忘”。怎样才能保持它呢?就要以任这自然的态度来生活。即一切随性去做,这样便无时无处不在佛性之中。
唐诗主情,宋诗主理,这是北宋欧阳修等文坛泰斗登上诗坛之后产生的倾向。正觉这首《绝句》,受此影响,重在说理。由小诗所受时代诗风影响也可以证明正觉生活的时代当在北宋末南宋初,这与小传中所述的简略身事正合。总之,小诗颇有禅趣,如与《金刚经》中川禅师的一则颂语:“滴水生冰信有之,绿杨芳草色依依。春花秋月无穷事,不妨闲听鹧鸪啼”比读,当不析自明。
绝句
水阔天长雁影孤,眠沙鸥鹭倚黄芦。
半收小雨西风冷,藜杖相将入画图。
普闻这首《绝句》,很好地体现了他在《诗论》中的观点。他在《诗论》中特别称赞杜甫、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等人的“意韵幽远,清癯雅丽”,并强调指出: “炼字莫如炼句,炼句或若得格; 格高本乎琢句,句高则格胜矣。天下之诗莫出乎二句,一曰意句,二曰境句。境句易琢,意句难制。境句人皆得之,独意句不得其妙者,盖不知其旨也。”在他看来,诗之写景造“境”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将其收束到一个妙“意” 中,终是平庸之作。这首《绝句》就很好地处理了 “境”与 “意”的关系。
前三句都可谓“境句”。“水阔天长雁影孤”,是由视觉所得的境句,侧重描写的是深秋季节的大空间背景,雁影之孤更衬托出这个大背景的寥阔。“眠沙鸥鹭倚黄芦”,也是由视觉所得的境句,但侧重描写的是深秋季节的一个特写短镜头,把它放在上句的大背景中显得境界很有层次感。“半收小雨西风冷”这一境句,逐渐由视觉所得过渡到触觉所得,使全诗所造之境又翻出一层新变化。特别是这个“冷”字,为逗开下句之“意”,作了很好的铺垫。在半收半下的秋雨中,西风之所以冷,这固然出自客观的自然之境,更重要的还是出自主观的诗人之意。于是很自然地过渡到第四句的“意句”。而“藜杖相将入画图”这句意句能“得其妙者”大约有三。一是揭示了主人公的身份。这位主人公只有“藜杖相将”,说明他是一个孤独者,这很符合释子的特征。二是揭示了主人公的气质。他虽然是一个孤独者,但他并不感到孤独,有一柄“藜杖”与他朝夕陪伴,出入相将就足够了。这很使人想起苏轼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气概。这又是深得禅道之人的特有气质,因而又很符合自己释子的特征。三是“入画图”这一巧妙的借喻,不但将上三句景色之美一笔收尽,起到很好的关合作用,而且将上三句对自然之境的感受轻灵地转入对艺术之意的体验,起到了境意双收的妙用。特别是因为一、二两境句有层次感、空间感,所以这里“入”字的意思也就很富层次感、空间感,它使读者仿佛看到作者正一步步走向沙岸,走向深空,进入到一个寥阔的世界中。
这样看来,作者在《诗论》中如此强调境与意的关系是不无道理的,他在这方面确有独到的体会,这首善于以意摄境的《绝句》即是明证。
绝句
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在 《宋诗纪事》 中,志南僧就留有这么一首诗,且还没有实质性的题目,只是借诗的形式题了一个不关意旨的诗题。然而就是这一首诗才使后人知其名,尤其是诗的后两句写二月天的轻柔凉美,生动而活脱,遂成为千古名句。看来,“新妇骑驴阿家牵”,当时无意,千古有情。一花开五叶,真的假不了。
诗写的是二月天里的真切感受。苍拙古木林中,于岸边树阴之处停下小船,系上缆绳,然后登上河岸。“短篷”即小舟。此一句开篇,似乎气氛有些阴郁。古木浓阴,置身其中,四围不免充溢颓腐之气,还会使人想起有古木便会有悲鸟,“悲鸟号古木”,似乎已经是定势了的一种意象组合。然而诗僧却就此打住,只是“古木阴中”,点到为止,化腐朽为神奇,不偏不倚地撑出一只小船来,且不紧不慢,停停当当地系在岸边,悠悠之中,很有方寸。虽不是“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 (储光羲《钓鱼湾》) 般的旖旎与幽丽,但却也别有一种清凉幽静的美感。系舟后,诗僧拄着藜杖,踏上小桥,奔桥东而去,古木斑驳,水流汩汩,似乎能听到诗僧拄藜杖击板桥的笃笃之声; 身影萧疏,一步步,隐入了桥东那另一个世界里。“杖藜”即为拐杖。宋代秦观《宁浦书事》诗之五曾有“身与杖藜为二,对月和影成三”句,将杖藜和自身来了一个意识的平等,互为依托。志南此诗更绝,杖藜在他意识中已远没有了 “我扶”之作用,也没有 “互扶”之作用,倒是反过来了,是“杖藜扶我”,诗僧自己成了不是杖藜的杖藜,乖乖,这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志南此说才正和常道。在平常人看来,拐杖是人扶着走路的,可正是靠人扶,拐杖才成为拐杖,如没有了人,拐杖何以得立,人可以不扶杖,但杖必须得扶人。因此,不是人扶杖藜,而是杖藜扶人,自然便是“杖藜扶我过桥东”了。禅者的观物方式,表面看去有悖逻辑和常理,但正是这种反常,才构成了神诗的奇趣,最终又归合常道。这其中,是深契事理的,只不过是比常人更深入一层,更有曲折之感。这就是禅家所说的“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的意蕴与真谛。
在带着节奏的 “笃笃”声中,杖藜扶着诗僧从桥西来到了桥东。桥东桥西,似乎给人两个世界之感,那边还是古木垂垂,浓阴郁郁,而这边却是杏花春雨,杨柳和风。“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两句是说在二月天里,沾人衣服直要潮湿的,是那杏花开时常下的杏花雨; 吹人脸面而不觉寒冷的,是那杨柳树中吹来的杨柳风。“杏花雨”是指清明时节杏花盛开,细雨润泽的景象。元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载:“《提要录》:杏花开时,正值清明前后,必有雨也,谓之杏花雨。”“杨柳风”指春天的微风。前蜀牛峤《更漏子》词云:“香阁掩;杏花红,月明杨柳风。”元代刘庭信《一枝花·春日送别》套曲:“丝丝杨柳风,点点梨花雨。”两句造语清秀疏淡,读来亲切可爱。杏花小雨,飘飘洒洒,雨夹着花的清香,花带着雨的湿润,展示了一个早春的迷濛天地。“欲湿”是似湿未湿,欲干犹湿,湿而不沾,沾而不淋的若即若离的状态。这正是杏花雨带给人轻梦一般的惬意和融洽。更兼那使柳丝依依,轻柔和煦,吹在脸上凉美而不寒冷的二月春风,真正构成了一个如诗如梦的境界。人置其中,看如烟杏花,如线杨柳;感如酥细雨,如丝和风,也正如蝉翼纱幕之后,欣赏明眸流睇之美,表达了对大自然的一种特殊感情。
宋人赵与虤《娱书堂诗话》卷上载:“僧志南能诗,朱文公尝跋其卷云:南诗清丽有余,格力闲暇,无蔬笋气。如云: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予深爱之。”朱熹能为其诗作跋,在当时实属不易,于此也可看出志南诗在当时的影响。朱熹以这首《绝句》为例,说其诗“无蔬笋气”。宋人论僧诗,“无蔬笋气”似乎是最高境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五十七引《西清诗话》云:“东坡言僧诗要无蔬笋气,固诗人龟鉴。”就是说僧诗要具清拨之韵,有本分家风,水边林下气象。看来志南此诗颇合标准,才赢得凡事讲究标准的朱熹的称赞。
实际上,有无 “蔬笋气”并不见得是论僧诗的最高标准。僧也罢,俗也罢,在诗之真谛上并没有截然的界限,“真诗人必不失僧侣心,真僧侣亦必有诗人心。” (钱钟书 《谈艺录》八八引法国白瑞蒙《诗醇》语) 志南此诗被人称赏,主要还是于平常景物中写出了一种诗趣,或是禅趣。那种桥东桥西的不同境界,那种“杖藜扶我”的反常合道,那种杏花雨、杨柳风的柔美清丽,既是平常的,又是满含诗味的。诚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所说:“平常非即惯常。譬如人莫不饮食,而知味者则鲜。凝神忘我而自觉,则未忘我也;及事过境迁,亡逋莫追,勉强揣摹,十不得一。微茫渺忽,言语道穷,故每行而不能知,知而不能言,不知其然而然。”同是平常景,不同的人便会有不同的 “言”,取得不同的审美收获。成佛成魔一念间,志南留下一首好诗,正是他桥东到桥西知其然而然的缘故。
绝句
烟翠松林碧玉湾,卷帘波影动清寒。
住山未必知山好,却是行人得细看。
这首诗写了诗人旅行途中,休憩于山间,凭窗远眺,不禁被山水美景所吸引,而恍然若有所悟。
“烟翠松林碧玉湾,卷帘波影动清寒。”这是诗人临窗眺望所见的画面。你看,缈缈的烟云,轻柔地缭绕于苍翠的松林间,朦胧而宁静,如梦似幻; 碧玉般清纯明净的水湾上,微波浮动,泛着粼粼的寒光,透出一股清冽之气。这是一幅多么空旷幽深、静谧素雅的山林图景! 那么幽,那么静,那么淡,那么雅,轻轻地散发出一股氤氲的禅意。诗人仿佛已 “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大凡在禅诗中,情感总是如此安详、澹泊; 节奏总是如此舒缓闲散; 色彩总是如此清幽、淡雅; 意象总是如此空灵寥落。林碧水寒,山空人寂,没有尘俗的喧嚣,没有人间的纷扰,恍如置身中天仙境,令人荣辱俱忘。静谧的自然,引出诗人独到的禅思。这里没有宗教的迷狂,有的只是智慧的闪光,有的只是对自然、对宇宙观照中的瞬间顿悟。
“住山未必知山好,却是行人得细看”,诗人深有领悟地说。有意深居于山间倒不一定能深刻地体味到山的好处,无意路过,反而能清楚地观赏到山林胜景,并真切地感受到个中真趣。诚如苏东坡所云: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错,观照需要有个 “距离”,人生也需要有个 “距离”,唯有跳出其外,方能见其真面目。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即此意。但在诗中,此句似另具深刻的禅理。“住山未必知山好”是因为有所执着;“倒是行人得细看”是因为无心而为。凡事应顺其自然,不能不求,亦不能刻意求之。能不能悟道主要不取决于外界环境,禅宗不要求某种特定的幽静环境(如山林)或特定的仪式规矩去坐禅修炼,而是认为任何执著于外在事物去追求精神超越,反而不可能超越,远不如在任何感性世界、任何感性经验中 ‘无所住心’ ——这即是超越。悟道当如“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一样自然;刻意求之,反不能悟。此禅家所谓“平常心是道”,“一切声色事物,过而不留,通而不滞,随缘自在,到处理成。” ( 《无门关》)
这首小诗清丽可爱,自然而成,信手拈来,宛若口语,语不涉禅,而含禅理。如果读者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该诗,定能获益非浅。
绝句
山腰一抹云,云起知何处?
急渡小桥寻,天风忽吹去。
这是一首顿悟真谛的禅诗,短短20字,犹如当头棒喝,惊醒愚顽。
“山腰一抹云,云起知何处?”诗中所述,本是山区日常所见之景。山腰飘浮着一片白云,却不知云起自何处。“急渡小桥寻,天风忽吹去。”诗人匆忙渡过小桥想去看个究竟,忽然一阵山风吹来,这片云不知又被风吹到哪里。这种寻而不得的情景,禅家语录里多有记述。据说禅宗传至日本后,有一尼师名叫千代能,在一个月明之夜用旧桶提水,偶有桶箍破裂而桶底脱落,豁然获得了大自在,做偈云:“扶持旧桶,桶底忽脱。桶里无水!水中无月!”冯坦这首绝句,其“寻云”和“参禅”亦可视为一件事。生死之真谛,犹如云之飘忽,来去无踪。忽然天风吹走这片浮云,天空一片澄明,诗人因而亦豁然获得了大自在,如果一任水绿山青,如盲似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亦可说是山中无云!
禅宗认为: 本来清静,不受一尘; 从来不失,何用追寻。未悟道之人,纵是如苦行僧青灯黄卷,整日坐禅潜修,亦无补于事。南宋廓庵禅师《十牛图》之一《寻牛》曰:“茫茫拨草去追寻,水阔山遥路更深。力尽神疲无处觅,但闻枫树晚蝉吟。”冯坦这首绝句,劝喻世人莫为“山腰一抹云”迷惑,这片云来去无踪,如果人们返照自己面目,就会发现如果返本还源,“水自茫茫花自红”(《十牛图》之九),真正得到解脱。
绝句
万木惊秋各自残,蛩声扶砌诉新寒。
西风不是吹黄落,要放青山与客看。
这是一首饶有机锋的禅诗。秋来草木凋零,一片肃杀,自宋玉《九辩》喟叹 “悲哉秋之为气也”起,文人骚客感物起兴,悲愁难遣,莫不借咏秋来抒写离愁伤悲。“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吴文英词《唐多令》) 迨至有宋一代,禅学公案的影响日深,诗人受其影响,好为翻案之语。如永嘉四灵中的赵师秀、徐玑之秋兴诗,都已跳出了悲秋的旧套。赵师秀《数日》诗云:“数日秋风欺病夫,尽吹黄叶下庭芜。林疏放得遥山出,又被云遮一半无。”徐玑《秋行》诗云:“红叶枯梨一两株,翛然秋思满山居。诗怀自叹多尘土,不似秋来木叶疏。”
汪若楫生于宋末,永嘉四灵对他的创作亦有影响,这首绝句与赵师秀的《数日》诗颇有相似之处,但理趣胜于赵诗。
“万木惊秋各自残,蛩声扶砌诉新寒。”残:凋残。蛩qiong:通“蛩”,即蟋蟀。扶砌: 沿着台阶。诉: 泣诉,啼叫。这两句诗以写景为主,透过诗人的一见一闻,抓住了秋天的特征。秋风瑟瑟,草木零落,蟋蟀因怕冷而迎风哀鸣。蟋蟀的哀鸣沿着台阶飞进屋子,似是向人哭诉秋气的肃杀。如此萧瑟的景象,显然流露出诗人对软弱无力的草木和蟋蟀的同情。下面,如果诗人不用强力挽住伤悲情绪的蔓延,很可能依然把这首诗写成悲秋伤怀的作品。
然而,诗人在开头两句描述了秋风的萧瑟,设置了令人伤悲的氛围,如何措词才能跳出悲秋的藩篱呢? 虽说翻案之语也能写出好诗,但前面所述秋景之零落已难强做翻案之语。此时,后两句仍写悲秋则为触犯,毫无新意可言;如强翻做颂秋则为相背,与前两句自相矛盾。背触之间,怎么办呢?谁知诗人笔锋一转,写出了“西风不是吹黄落,要放青山与客看”的绝妙诗句。西风:即秋风。黄落: 枯枝落叶。放: 敞开。客: 泛指行人。诗人精通禅理,运用禅宗执中而不拘于中的思想,直接揭示秋风吹落草木的目的,即让青山露出本来面目供人观看,劝喻众人不要为西风凋残草木而伤悲,也不要故意颂扬秋气之肃杀。禅宗认为: 看事物不过背触两边,唯不死于两边,执中而不拘于中才能合于禅宗所谓既悟其有,又悟其无的至境。
诗人这首秋兴绝句,跳出了悲秋伤怀的旧套而又非单纯的翻案文章,毫无疑问,这是诗人禅悟所带来的结果,反过来说,当我们读这首诗时,也应该认真想一想,从中体悟这首诗所蕴含的禅宗不执于两边的思想,像古代印度禅师湿婆所说的那样:“思维知与不知,有与没有。而后离开你可能执着的两边。”(《中道》三六)
绝句
诗体的一种。又称绝诗、截句和断句。一首四句,或五言,或七言,也有六言的,平仄和押韵都有一定的格式。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一:“绝句者,一句一绝,起于《四时咏》,‘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是也。”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云:“五言绝始汉人小诗,而盛于齐、梁。七言绝起自齐、梁间,至唐初四杰后始成调。”这是对绝句的名称和渊源所作的说明。至于绝句的作法,论者甚众。元杨载《诗法家数》云:“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参阅“截句”、“断句”。
《绝句》
春朝湖上风兼雨,世事如花落又开。
退省闭门真乐处,闲云终日去还来。
这首七绝原载 《海盐图经》。
从首句“春朝湖上风兼雨”所写春朝、湖上、风、雨看,似是写景,然与下边三句所写内容联系起来分析,当是以比兴手法引出诗中所写的人间事理。诗写的是春天,正是花开的季节,而由于风吹雨打,花开花落是很自然的事。诗人在此用花开花落来喻世事之无常迁流。佛教认为“诸行无常”,即一切事物有生必有死,不能保持其永久的生命。一切宗教都追求永恒的存在,佛教也不例外。那么,如何在无常迁流的世界中追求永恒呢?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生于这个世界,跳出这个世界。这就是佛教所说的涅槃解脱。
“退省闭门真乐处”句,是写正觉掩门修道的情趣与感受。“退省”,指按禅宗“内悟自心”的方式去悟禅;“闭门”指远离尘世之一切喧嚣烦恼。故曰 “真乐处”。
“闲云终日去还来”,表面看是写正觉常见的自然景象,实则是她入禅为尼之后的心理写照。禅宗常用 “白云”喻任运自然的修行生活。佛徒主张排除世间一切欲望,努力自悟本性。自悟了本性之后,要时时注意保持它,“莫失莫忘”。怎样才能保持它呢?就要以任这自然的态度来生活。即一切随性去做,这样便无时无处不在佛性之中。
唐诗主情,宋诗主理,这是北宋欧阳修等文坛泰斗登上诗坛之后产生的倾向。正觉这首《绝句》,受此影响,重在说理。由小诗所受时代诗风影响也可以证明正觉生活的时代当在北宋末南宋初,这与小传中所述的简略身事正合。总之,小诗颇有禅趣,如与《金刚经》中川禅师的一则颂语:“滴水生冰信有之,绿杨芳草色依依。春花秋月无穷事,不妨闲听鹧鸪啼”比读,当不析自明。
绝句
〔1〕原诗四首:写于广德二年春天,杜甫回到成都草堂。这一首是第三首,描写成都春日景物风光。
〔2〕窗含:在窗口里嵌着,实指从窗口望出所见景物若风景画嵌入镜框。西岭:指岷山,山顶积雪长年不融化,故称“千秋雪”。
〔3〕东吴:原指三国时建都于建业(今南京)的孙氏政权,后亦用以泛指今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万里船:杜甫草堂东面不远的锦江上,有一座“万里桥”,古时由成都东下都从此上船。三国时诸葛亮送费袆出使东吴,曾在此饯行,费袆说:“万里之行,始于此桥。”万里桥由此而得名。杜甫此诗“万里船”化用此典。
这首七绝历来为世人称道,在于构思与对仗之精巧。描写春日景物风光,色彩清丽,幽美如画,于恬静中有动态,于适意中而面千秋、见万里。《杜臆》曰:“草堂多竹树,境亦超旷,故鸟鸣鹭飞、与物俱适;面对西山,古雪相映,对之不厌,此与拄笏看爽气者同趣;门泊吴船,即公诗‘平生江海心,夙昔具扁舟’是也。历来绝句中两联俱对者甚稀,此诗不但两联对仗,名词、动词、形容词、方位词、数目词,连颜色都对偶工整,做到了细类相对。古人教对偶多以此为范。像这样一诗两联精妙的对偶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古人称为“奇作”、“绝唱”。杜甫以律诗名世,绝句虽不多,也见功力。
绝句
数日秋风欺病夫, 尽吹黄叶下庭芜。
林疏放得远山出, 又被云遮一半无。
本诗讲缺陷美之理。
首二句言秋风欺己,后二句言秋云欺己。诗称“病夫”,当不得远游。故此,诗人对秋景的欣赏只能局限在庭院之中,而不能远行入山。可是,无端“秋风”偏偏要欺负我这个病夫。一派好端端的秋色,却被“数日秋风”搞得“黄叶”遍地,真是大煞风景。好不容易盼到风住叶尽, “远山”该露出真面目了, “又被云遮一半无”,只能看到一半而难以窥见全貌。诗篇用“欺”,用“尽吹”,用“又被”,写出了诗人的懊恼之情。
诗人眺望远山,是期望一睹远山全景,因此,当“黄叶”落尽,山林稀疏之际,诗篇用“放得”二字写尽了远山即将现出全貌之时诗人的欣喜之情,可是,秋云又从中作梗,令人不无遗憾。看来,诗人所追求的是“远山”的全貌,任何遮蔽,无论它来自树叶,还是秋云,都使诗人感到不快!殊不知世问如此完美之景确不多见!大量存在的美都是缺陷美。此其一。其二,美在于发现。“远山”全貌固然可爱,云遮半山也未必不美;绿树葱茏的确很美,“下西风黄叶纷飞”也未必不美!美是多样的!
绝句
这是对官小架大者的讽刺诗。黄钧宰《金壶七墨戏墨》云: “官职卑高不足较,独官卑而昂然自大者,甚可厌也。曩见一绝云云。”
诗意略谓: 一艘大船,在航道中抢先行驶(争上游),横冲直撞,势派极盛,船上连跟班的仆人,也都锦衣轻裘,鲜明亮丽,好不令人眼热!看样子,这是什么大官巡行。然仔细辨认旗幡(日观)和灯笼(夜观)上的字,原来船主才担任了不入流的小官。才任卑职便趾高气扬,实在令人厌憎。
何谓“未入流”?即排不上品级的官吏。《西游记》中有一段述写很有意思,不妨录以备考: 正在欢饮之间,猴王忽停杯问曰: “我这(弼马温)是个甚么官衔?”众曰: “官名就是此了。”又问: “此官是个几品?”众道: “没有品从。”猴王道: “没品,想是大之极也。”众道: “不大,不大,只唤做‘未入流’。”猴王道: “怎么叫做 ‘未入流’?”众道: “末等。这样官儿,最低最小,只可与他看马。……”
“未入流”的小官,都能如此豪横,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社会的官是统治者,与民身份已不平等,因而熬上当官的资格,便要力求与民区分开来,摆排场自是最省事的办法,所谓“堂上一呼,堂下百诺”,便是当时人们对官的认识。于是乎船行江中,不但体形要大,即诗中所云 “大舰峨峨”,而且派头要足,即诗中所云“拥上游”(抢道先行),至于是否扰民,作官者便不加考虑了。人们厌弃此等角色,也就毫不足怪了。明代有首民歌《朝天子·咏喇叭》便讥抨了官船扰民的社会现象:“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您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得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军民对争先抢道、来往如麻的官船,连“真共假”都无暇辨别,哪里敢去计较什么 “大与小”呢?大官小官都是统治者,“未入流” 的官员摆架子,何足为怪。
清朝初年有首诗《嘲鸿胪寺某序班》,还只是提及他个人品行不端,“小器那能容大物”,本诗则是兼有社会意义,不妨参照阅读。刚任小官便得意忘形的琐屑小人固然可鄙,给小官讲势派提供土壤的封建制度更可恨。畸形的社会,才能造就这扭曲的人品。
绝句
万木惊秋各自残, 声抉砌诉新寒。
西风不是吹黄落, 要放青山与客看。
这首小诗写的风趣幽默。
首句写秋气之威力。本来,严秋到来,万木落叶,可是,作者为渲染秋气之威严,偏偏写“万木”惊慑于秋气,不等秋风拂之而落,而是各自互相摧残, 自陨其叶,这是何等的威力啊!第二句紧承首句,继续渲染秋气之威严。但是,在写法上,却另辟蹊径,不写“万木”,而写寒蛩(即“”)。诗中用“抉砌”,用“诉新寒”,写寒蛩畏缩在台阶之上诉说着寒凉带来的痛苦。二句用典型之景,简洁之笔,写尽了秋气的威严。
面对如此秋气,诗人却用诙谐之笔,高唱“西风不是吹黄落,要放青山与客看。”秋风不是非要把树叶吹黄吹落,而是要扫掉遮蔽青山的树叶,好让客人观看。
同样是面对秋气,有人黯然伤神,有人引吭高歌,关键是观景者自身的审美情趣所致。只有培养起积极健康的审美情趣,才能积极地面对人生。
绝句
杜 甫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原诗今译】
两只黄莺在翠绿的柳丛中溜溜啼啭,
一行白鹭扑噜噜地飞向了湛湛蓝天。
窗外西眺,是岷山千年不变的积雪,
倚门东望,停泊着东吴的万里航船。
【鉴赏提示】
杜甫的诗多是具有博大精深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千古绝唱,其风格亦以沉郁顿挫为主,但也有不少反映美好大自然的不朽佳作,清新流畅,充满了诗情画意,这首诗可以说就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首诗是唐广德二年(764)杜甫在成都时所作。由于安史之乱,杜甫于乾元二年(759)冬天辗转来到成都。上元元年(760)开始,在成都西郊临江之处营建了著名的“浣花草堂”。宝应二年(762),杜甫的好友成都尹严武入朝,蜀中发生动乱,杜甫不得不避往梓州。广德二年,正当杜甫准备离开蜀中时,严武还镇成都。得知这一消息,杜甫特别高兴,于是在这年二月也返回了成都。回到成都,杜甫心情极佳,便在他的草堂居所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
诗的前两句从所住草堂就近的见闻写起,由近及远。黄鹂即黄莺; 白鹭即鹭鸶鸟,因羽色纯白,又叫白鹭。时当三月,春意正浓,诗人在草堂内听到了两只黄莺在新绿的柳枝丛中相对欢鸣,不由得兴致大发,起而观赏。这时他又看到了一群长腿白鹭排成一行从草堂前的江面上飞上了春意融融的蓝色晴空。黄莺的叫声婉转动听,白鹭的飞翔姿态悠雅,生机勃发的新柳给人间带来了新生命的希望,万里晴好的蓝天则给人展现了更广阔的前景,这有声有色、有动有静、近远层递展开又协调统一的春日景象,真是一幅美妙而又惬意的醉春图呵! 诗人通过这幅清新绚丽、春意盎然的图景的描绘,表达了无比轻松愉悦的心情。
后两句接着前两句继续写景。所不同的是前两句所写景象为由近及远和以动为主的,后两句则纯写远方静景,又将它们由远拉近。诗人观赏了草堂近前的翠柳黄莺和远方的白鹭蓝天之后,视线从天上下移而至远处的雪岭行船。下句“门泊”与此理同。西岭,窗西之山岭,指雪岭,松潘县南的雪栏山,积雪终年不化,故名。东吴,此指江浙一带。万里船,指将去万里之外的东吴的船,一说为来自万里之外的东吴的船,亦通。西山雪岭,平时难见,只有在天气晴好时才清晰可见。当此心情愉悦之时,诗人自窗远眺,看到雪山。用一“含”字,远景被拉到近前,雪岭恰如镶嵌在窗框中的一幅雪山春图,妙不可言! 江船在草堂居所本不难见,这里说个“万里船”,却是意味深长,诗人的无尽感怀和思绪都包含在了其中。船将去万里之遥的东吴(或曰船从万里之遥的东吴而来),说明战乱已经止息,交通恢复了。诗人一直本有离蜀游吴之意,他由门前远处的船只想到东吴,也说明了这个夙愿。同时,他更把眼界、心境伸向了无穷远大的空间。人在草堂,心游万里,思绪联翩,把草堂美景与天下安泰联系了起来,对草堂这个美妙所在的赞赏与离乱平定之后更深一层的喜悦情怀和遐远深刻的感触便完美地融在了一起。
这首诗从写法上来说,极富特色。首先是对仗非常工整。前两句和后两句都是典型而且极好的对仗句,其事物、词性,无论哪一方面,真是无一不对而又无一不工。这种对仗,使得事物之间既紧密相连,更彼此烘托,有力地加强了表达效果。其次,由于诗人对绘画深有研究并能以画法入诗,所以本诗的构图更独具匠心,具有清新而又浓郁的诗情画意。其构图既有着色的协调与互相映衬,如黄—翠,白—青,黄—白,翠—青。又有布局的巧妙与远近交错成文,如黄鹂、翠柳为近,白鹭、青天为远;窗含、门泊近说,西岭、东吴指远; 而窗含、门泊的把远景近写所增强于人的欣赏兴趣,千秋、万里所含时间之久与空间之广所融入的诗人远近融合的遐思深意,则又不是画法所能尽现的了,除着色与布局之外,构图的独到还表现在动静的巧妙安排方面。如翠柳、青天是静的背景,黄鹂鸣、白鹭上为动的点缀,虽是点缀,实为中心,它们使得画面一下子活起来了,可谓似分实合,缺一即呆。至于窗含千秋雪、门泊万里船,表面是静,实际是动,因为它们把人的思绪引入了无尽的时空,起伏无息,其动静已融合得浑然一体了。这无形中增加了诗的美感与魅力。由于这些,本诗真是一句一图画,而四句又合成一幅完整的图画,难怪后人要称杜甫的诗是“图经”了。第三,本诗遣词造句语出自然,不见丝毫雕饰,读来则明白如话,品之则意味深长,诚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了。这些写法上的特色,显示了诗人极其深厚的艺术功力。
绝句
书当快意读易尽, 客有可人期不来。
世事相违每如此, 好怀百岁几回开。
这是一首讲人生适意之时太少的诗篇。
诗的首二句连举二例。一为读书,一为见客。就读书而言,真正让人满意,读起来能获得极大精神享受的书籍,往往很快就读完了。就见客而言,一些让人见后能使自己非常满意的客人,往往盼不来。诗篇以“快意”与“易近”连用,以“可人”和“不来”连用,诉说了人生适意之时太少带给诗人的痛苦。
诗的后二句举此以例余,由读书、见客上升到“世事”。作者由此悟出,人世间的事情让人难以称心者太多了,一生中真正令人开怀畅意的时光能有多少呢?
人生有“快意”“可人”之时,亦有不尽人意之时,这正是人生最正常的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诚然,人们都渴盼自己能多一点“快意”“可人”,少一点不尽人意。但是,二者也只能是多与少,而不可能是有与无。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方可在“快意”“可人”之时保持冷静,在不尽人意之时达观处世。
绝句
僧志南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原诗今译】
在幽暗的老树下系住小船,
拄着拐杖,走向小桥东边。
飘飘的春雨将要打湿衣裳,
风儿不冷,轻轻抚着脸面。
【鉴赏提示】
一首诗,重要的在于创造出一种意境,并能引导读者进入诗作的艺术世界中去领会、感受,获得艺术欣赏的趣味。对于写景小诗来说,更是如此。
托名王昌龄所作的《诗格》中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三曰意境……”这里说的“三境”其实即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意境,只是把偏重于写山水的称为物境,偏重于抒情的称为情境,偏重于言志的称为意境。对于写景诗的作者来说,他首先要能看出自然界中山水“极丽绝秀”,即景物之美的一面; 其次,则是要描写出山水之美,“故得形似”,是说要做到形象化的表现。但仅有这两点还不够,要能“神之于心”“然后用思”,即着上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写出作者的独特感受。这样的作品才不至于变成刻板的纯客观描摹,才会具有一种飞动而传神的灵性。
僧人志南的这首《绝句》好就好在:他不仅看到了春风细雨之中的野外景物,在寻常环境中发现了美的诗意,而且用形象的描写表现了这种美; 他不仅艺术地再现了自然之美,而且还渗透着自己的独特感受。请看:
春天的细雨飘飘洒洒,天地间一片安静和谐的气氛。一位老和尚撑着有篷的小船过来了,他在河边的一棵古树下系上缆绳把船停下来,然后上岸,向着小桥的东边走去。他年纪高迈,走得很慢,那根藜茎做成的手杖好像懂事的徒弟一般,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走路。濛濛春雨在不停地落下,夹着风儿迎面洒来,连僧袍也渐渐潮湿了。但他并不着急,心想:在这杏花盛开的季节,这场春雨总不会像绵绵秋雨那样下得太大太久的。好在,这拂面的东风能催得杨柳发芽,抽枝吐絮,吹在身上也并不很冷……他微笑了。这是多么惬意的一次春游啊!
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平淡得像一幅淡墨风景画,然而,这平淡却使我们读后难忘,“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绝句
崆峒访道至湘湖, 万卷诗书看转愚。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夏氏此诗的后二句,即“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极为有名,《水浒传》第三十六回,及许多明清小说常常引用之。“铁鞋”固然无法穿上行走,但是“铁鞋”尚且“踏破”,足见耗费时间和精力之多,而“无觅处”三字轻轻一转,则“访道”之难可见,下句却以“得来”“不费功夫”写其易,而“不费功夫”四字之上再冠从“全”字,则极写其易。
但是,仅有此二句仍不成其为好诗,此诗之成功实在离不开前二句的铺垫。首句的“访道”二字交代了“踏破铁鞋”的缘由。 “崆峒”属六盘山,在今甘肃省平凉县西。“崆峒”“至湘湖”,即从今甘肃到今湖南,诗人之意在于强调其行路之远。次句的“万卷诗书”写其为“访道”而遍读全书,诗人之意乃在强调其搜寻之广。而“看转愚”三字则否定了在“万卷诗书”中“访道”的方向。中国历来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之语,但是此诗的前二句既否定了行万里路之“访道”,又否定了读万卷书的“访道”,而强调了兴悟与灵感在“访道”中的决定作用。
南宋词人辛弃疾[青玉案] 《东风夜放》词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引用辛词的这几句说明做学问、干事业的最高境界。王国维赋予辛词以新意。王氏之新意实和此诗之意相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踏破铁鞋”,可谓艰难至极,而“得来全不费功夫”则似乎又容易至极。但是,这易是难中之易,是先难之后的易。如果没有“踏破铁鞋”,那么也就决不会有“得来全不费功夫”。换言之,如果没有“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么也就不会发现“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崆峒访道至湘湖”是一种代价,“万卷诗书看转愚”也是一种代价。唯其有了这两个“踏破铁鞋”,即“崆峒”“至湘湖”的“踏破铁鞋”,和“万卷诗书”的书山中的“踏破铁鞋”,这才为“访道”至得道做好了准备,即知识结构上的准备与学识上的准备,这才有可能获得兴悟与灵感。可见,兴悟乃长期积累的点燃,灵感是长期思索的闪光。易是难后之易,难是获易的必然。
绝句
杜甫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先唐以五绝写景,有所谓“一时而四景皆列”的手法,如吴筠诗:“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这种手法写景,工致如画,杜甫比较偏爱。广德二年作于成都草堂的“迟日江山丽”绝句,即运用此法。它四句皆对,工整自然。
“迟日江山丽”。《诗经·豳风·七月》云:“春日迟迟”,是说仲春的日子,白昼一天长似一天。这时风和日丽,山河特别秀美可爱。“迟日”二字笼罩全篇,给人以温暖明媚之感。
“春风花草香”。前句写春光明媚,此句则写春的气息。前句偏于触觉,此句偏于嗅觉。因“日”见“丽”,凭“风”传“香”,用字工稳可喜,又表现出景物间的联系。
前二句着力写春天给人的总体感受,较为宏观,有如画图的阔大背景。后二句则着力刻划一二细节,较具体而微。它写的是小径与溪边的景物。“泥融”、“沙暖”都承“迟日”句来。“飞燕子”、“睡鸳鸯”则写出两种鸟儿,一动一静,它们分别与“泥融”、“沙暖”搭配,意蕴更加丰富。盖燕子春来忙做窠,春来土湿,它们啄泥芳径,又复飞去。鸳鸯成双作对,因春水犹寒而日照沙暖,它们便交颈而眠,贪享春天的温暖。通过两种鸟儿的动静刻画,反映了春天的勃勃生机。既从大处着眼,又从细处落墨,有联系又有对照,虽一句一景,但不零乱、单调。“丽”、“香”、“融”、“暖”等形容字,下得准确,堪称诗眼。通过美好春光的描绘,反映了饱经丧乱漂泊之苦的诗人在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中的喜悦心情。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公元762年,成都尹严武入朝,蜀中发生动乱,杜甫一度避往梓州,翌年安史之乱平定,再过一年,严武还镇成都。杜甫得知这位故人的消息,也跟着回到成都草堂。这时他的心情特别好,面对这生气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写下了一组即景小诗。此其一。
诗的上联是一组对仗句。草堂周围多柳,翠绿的柳枝上有成对黄鹂在欢唱,一派愉悦景象,有声有色,构成了新鲜而优美的意境。“两个黄鹂”,成双成对,呈现一片生机,具有喜庆的意味。次句写蓝天上的白鹭在自由飞翔。晴空万里,一碧如洗,白鹭在“青天”映衬下,色彩极其鲜明。两句中一连用了“黄”、“翠”、“白”、“青”四种鲜明的颜色,织成一幅绚丽的图景;首句还有声音的描写,传达出无比欢快的感情。
诗的下联也由对仗句构成。上句写凭窗远眺西岭雪山。岭上积雪终年不化,故称“千秋雪”。而雪山在天气不好时见不到,只有空气清澄的晴日,它才清晰可见。用一“含”字,此景仿佛是嵌在窗框中的一幅图画,近在目前。观赏到如此难得见到的美景,诗人心情的舒畅不言而喻。下句再写向门外一瞥,可以见到停泊在江岸边的船只。江船本是常见的。但“万里船”三字却意味深长。因为它们来自“东吴”。当人们想到这些船只行将开行,沿岷江、穿三峡,直达长江下游时,就会觉得很不平常。因为多年战乱,水陆交通为兵戈阻绝,船只是不能畅行万里的。而战乱平定,交通恢复才看到来自东吴的船只,诗人也“青春作伴好还乡”了,怎不叫人喜上心头呢?“万里船”与“千秋雪”相对,一言空间之广,一言时间之久。诗人身在草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次何等开阔!
全诗乍看一句一景,而随着视线的游移、景物的转换,江船的出现,乡情的贯穿,四句景语就构成了完整的意境。
绝句
- 原文
- 拼音
- 繁体
- 《绝句》.[唐].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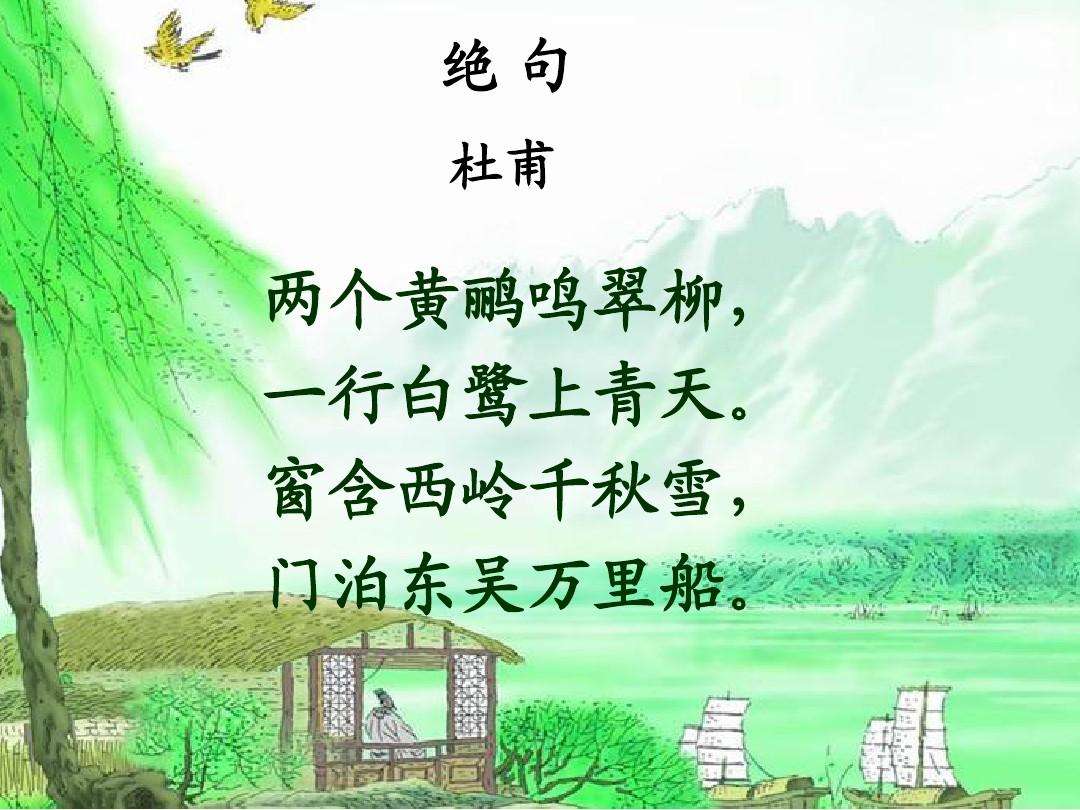
- 《 jué jù 》《 绝 句 》.[ tánɡ ]. lǐ bái..[ 唐 ]. 李 白 .liǎnɡ ɡè huánɡ lí mínɡ cuì liǔ , yì xínɡ bái lù shànɡ qīnɡ tiān 。两 个 黄 鹂 鸣 翠 柳 , 一 行 白 鹭 上 青 天 。chuānɡ hán xī lǐnɡ qiān qiū xuě , mén bó dōnɡ wú wàn lǐ chuán 。窗 含 西 岭 千 秋 雪 , 门 泊 东 吴 万 里 船 。
- 《絕句》.[唐].李白.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 译文
- 注释
- 诗评
- 【译文】 两个黄莺儿在绿柳间婉啭歌唱,一队白鹭鸶直飞上碧空蓝天。窗口嵌含着西岭上经年不化的积雪,门外码头停泊着将驶向遥远的东吴的船。
【逐句翻译】
两个黄鹂鸣翠柳,成对的黄鹂在翠柳枝上欢叫,
一行白鹭上青天。成行的白鹭飞上如洗的蓝天。窗含西岭千秋雪,窗框里嵌着千秋积雪的西岭,门泊东吴万里船。大门外泊着万里东吴的航船。 - ①鸣:叫。②含:窗户对着西边的山脉,就像把远山装在窗框里一样。③千秋雪:指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④泊:停船。⑤东吴:三国时候孙权在江南建立吴国,也称东吴。这里指现在的江苏一带。
- 【集评】 宋·范季随:“杜少陵诗云: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极尽写物之工。”(《诗人玉屑》卷十四)宋·程大昌:“诗思丰狭,自其胸中来。若思同而句韵殊者,皆像其人,不可强求也。张祜送人游云南,固尝张大其境矣,曰‘江连万里海,峡入一条天’。至老杜则曰‘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以较祜语,雄伟而又优裕矣。”(《演繁露·续集》卷四)明·王嗣奭:“草堂多竹树,境亦超旷,故鸟鸣鹭飞,与物俱适,窗对西山,古雪相映,对之不厌,此与拄笏看爽气者同趣。门泊吴船,即公诗‘公生江海心,夙昔具扁舟’是也。公盖尝思吴,今安则可居,乱则可去,去亦不恶,何适如之!”(《杜臆》卷四)清·何焯:“言鸟犹飞鸣得所。蜀中久乱,何可复恋?俟雪消水生,便思放船下峡也。”(《义门读书记》卷五十五)清·浦起龙:“‘鹂’止‘鹭’飞,何滞与旷之不齐也?今‘西岭’多故,而‘东吴’可游,其亦可远举乎?盖去蜀乃公素志,而安蜀则严公本职也。蜀安则身安,作者有深望焉。上兴下赋,意本一串。注家以四景释之,浅矣。”(《读杜心解》卷六)
- 赏析一
- 赏析二
- 赏析三
- 这是在中国最为流传的小诗之一。它通俗易懂,平白如话,却又深含了诗人的审美理想, 极受文人学者所推许, 可说是以俗为雅, 雅俗共赏。试看诗人以二十八字的篇幅勾勒出的画卷里,深蕴着多少层次的矛盾统一, 它是多与少、高与低、远与近、动与静, 以及色彩上的深与浅,审美思潮上的自然与人为等多侧面、多角度的对立统一。譬如说,诗人说“两个黄鹂”,这是以少发端,而说“一行白鹭”则是以多相映; 说 “两个黄鹂鸣翠柳”, 这是从低景画出, 而 “一行白鹭上青天”,则是引领你的目光飞向极远无垠的青空,这又是高处之景。“窗含西岭千秋雪”,此句看似写远——远处山岭上积聚的千秋不化之雪,然而,诗人却把它装入 “窗含”的框嵌之中, 这是远景近写; 而 “门泊东吴万里船”,又恰恰相反,诗人写的是“门泊”——门前停泊的船只,这是一个近景, 但此船正欲扬帆远航,它要东行万里,直抵东吴,“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下洛阳”,诗人奔腾跳跃的想象之羽翅,要引领你到无限遥远的异乡漫游!这样,“门泊”这一近景中又蕴含了远景,这是近景远写吧!你看,诗人这看似平朴无奇的四句话, 是不是一幅构图严谨、想象奇妙的画卷呢?不仅如此,这幅画卷还是动与静、时间与空间的和谐统一。你听,“两个黄鹂鸣翠柳”,它要诉诸听觉,但它们相对于 “上青天”的白鹭,则是在静境之中——它们静静地、安详地在翠柳碧叶之间歌唱;而 “一行白鹭上青天”,则是纯粹诉诸视觉,它们似乎是无声地、静静地凝止于天空,但诗人用一个 “上”字,就把这个画面点活了——白鹭扑打着羽翅,飞向蔚蓝的天空。可说是动中有静、静中寓动吧!“千秋雪”三字,极言时间之无限,而 “万里船”三字, 则与上联呼应,展示了空间的无际无垠。这样,就使诗人身之所在之草堂, 目之所见之景物, 时接千载而目通万里!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以 “自然艺术”和 “人为艺术”来界分两种不同性质的艺术。“绝句”这种格律诗,无疑地是要更多地带有人工雕琢之迹,当属 “人工艺术”,但在 “清水出芙容,天然去雕饰”的时代审美思潮中被推许为诗坛盟主的老杜,无疑又要追求自然之美,这就形成了两种艺术的完美结合与统一。这首小诗极合格律,却又极为自然; 反之,这些诗句似乎是信手拈来,却又极含匠心。譬如此诗四句,字字都是对仗的:“两个”与 “一行”、“黄鹂”对 “白鹭”、“鸣”对 “上”等等,无不工稳精湛而又自然生成;同时,在这 “带着镣铐的舞蹈”(闻一多语)里,诗人画笔挥洒,酣畅淋漓, 那柳之青翠, 天之湛蓝、雪之晶莹、水之澄清, 加以“黄鹂”、“白鹭”飞舞鸣唱其间, 真可谓绚烂夺目, 令人魂动神摇了。我国由唐入宋,渐次形成了追求 “大巧之朴”的美学思潮,如王安石说“看似平淡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黄庭坚推崇“平淡而山高水深”,大概主要是对李杜等这一类诗作的总结吧!
- 广德二年(764)春,杜甫闻知其好友严武复为东西川节度使,还镇成都。严武屡屡来信相邀,于是杜甫携家由梓州重返成都草堂。这一时期,诗人生活较为安定,心情较舒畅。成都初春,花红柳绿,生机盎然。触发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深深赞美之情,写下了这一组即景小诗。全诗共四首,这是其中第三首。苏轼曾以“诗中有画”评赏王维山水之作,而这首绝句似乎更像一组清新淡雅的水粉画,并列的四扇屏。分看一幅一景,合起来又是一大幅意境开阔、情趣和谐的画面。“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柳丝新绿,翠芽初吐,枝条婀娜迎风摇曳,两个黄鹂飞戏其间,时时发出清脆的欢唱。这幅画或可叫作“柳岸闻莺”。晴空万里,一碧如洗,白鹭点点,列队翱翔。这一幅或可叫作 “春回雁归”。两句之中一连用了 “黄”、“翠”、“白”、“青”四种颜色,把那风和日丽的明媚春光描绘得绚丽多姿。一般说,诗家较忌用颜色字,用多了显得柔糜浮艳,杜诗这里用后却取得了意外的效果,因为这四种颜色基调和谐,清淡素雅,令人倍感新鲜明快,赏心悦目。这一联对仗工稳而不失板滞,句中运用了两个动词“鸣”、“上”。一个表声响,一个表动态,声动相间,显得参差错落,诗情画意被渲染得有声有色。“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也是对仗极工的联句,这一联妙在“含”字上,诗中嵌一“含”字,犹如画龙点睛,把整个后两句点活了。西山雪岭,峰顶积雪终年不化,但距成都甚是遥远,平时是望不到的,只有万里无云空气清澄的日子才能隐约显露出来。诗人在屋内偶然一瞥,透过窗口,却有幸看到了。读这一句要注意诗人在屋内的位置角度,不是凭窗眺望,而是距窗较远,否则“含” 字无着落。西岭雪峰仿佛是镶嵌在室内的一幅图画,近在眼前,诗人感到特别赏心悦目。接着,诗人的视线由窗口又移向门前,门前停泊着通向下江东吴的船只,由成都沿岷江穿三峡,过两湖到东吴,行程数千里。这句写眼前景,但也流露出诗人心中事,战乱已平息,可以出川返乡了,诗人的欢愉心情更增加了一层。“千秋”、“万里” 均非实指,一言时间之久,一言空间之远,足知诗人的联想是何等开阔而豁达。这一联句中的两个动词 “含”、“泊”,亦最见诗人匠心。“含” 如口中衔含,这样把静物说活;“泊” 字不仅是停靠,更有摇荡漂泊的动感。四句一句一景,但诗人的视距不尽相同,一近一远,又一远一近,交相辉映,从不同角度把一幅有山有水、有声有色的草堂春意图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恬静幽雅的艺术享受。杜诗以律为绝,这首诗当是最典型的一例。前人评价不一,有人疵之为 “断锦裂绘之类”(胡应麟《诗薮》卷六)。无疑,这首诗在形式上很像七言律诗的颔、颈两联。但确实是一首意境和谐、结构完整的诗。设想,又有谁能再补上首尾两联?如有能者,定为蛇足!
- 善于描写大自然,是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之一。他有许多山水诗、田园诗和即景即情的小诗,都写得自成家数,十分精绝。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他兼容并包,撷取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艺术成果,又经过自己的提炼、创造,写出了许多“清词丽句”,把景物诗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步。这首诗是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春天,杜甫在成都草堂时写的。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入蜀,到成都后得到了友人严武的帮助,次年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建立了新居,他自称“浣花草堂”。诗人在久经乱离之后有了安静的栖身之处,心情是悠然自适的。这首绝句就通过描绘自然景物,展示优美开阔的画面,抒发了当时的舒畅情怀。它圆熟精工,独具风采,是杜甫绝句中的珍品,在艺术表现上有三个特色:其一,结构精巧,意境完整。全诗四个诗句,一句一景,各臻其妙。首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是一幅近处的动景——阳春三月,绿柳摇曳,在那青翠的枝条上一对黄莺鸟儿跳上跳下,婉啭和鸣。这里写黄鹂的活泼欢跃,衬托出了人的悠然闲适。第二句“一行白鹭上青天”,是一幅远处的动景——碧波粼粼的江面上,一行白鹭展翅飞上了蓝天,那齐整不乱的队形,那凌空自如的姿态,都牵引起诗人无限的情思。第三句“窗含西岭千秋雪”,是一幅远处的静景——从窗口远远望去,西面的岷山巍峨逶迤,山峰上白皑皑的积雪,终古不化。凭窗凝目,令人感到时间的悠久,宇宙的无穷。第四句“门泊东吴万里船”,是一幅近处的静景——门前江面空阔,江水浩荡东流,码头上停泊着将要向东吴进发的船只。船一起锚就要到万里之外,诗句虽然写的是门前的泊船,却大有咫尺万里之势。整首诗由近及远,又由远及近,由低而高,又由高而低,远近映衬,动静配合,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意境开阔的画面,既生动地描绘了景物,也形象地袒露了诗人的情怀。其二,画面优美,色彩鲜明。诗是无形的画,诗人在这首诗中描绘形象、展现画面都十分讲究色彩的运用。作者选取那些富有春天色彩的景物,并用表示色彩的词语加以巧妙的修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就是一联铺彩着色十分和谐的诗句。“黄”鹂、“翠”柳、“白”鹭、“青”天,绿中带黄,青中有白,色彩界限既分明,画面的色彩也异常柔和。色彩美增添了诗的意境美,生动地衬托出了诗人欢愉的心情。其三,对仗严整,语言精练自然。杜甫这首诗四句两联皆成对偶,黄鹂——白鹭,窗含——门泊,千秋——万里……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各自相对,非常工稳,造成了诗歌的整齐美。四句皆对,这在绝句中是少见的,诗人刻意求工,但诗句并不呆板。整首诗读来节奏轻快,音韵浏亮,仿佛从笔端自然流出,这是诗人艺术技巧成熟的表现。
绝句
- 原文
- 拼音
- 繁体
- 《绝句》.[唐].杜甫.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风起春城暮,高楼鼓角悲。
- 《 jué jù 》《 绝 句 》.[ tánɡ ]. dù fǔ..[ 唐 ]. 杜 甫.jiānɡ biān tà qīnɡ bà , huí shǒu jiàn jīnɡ qí 。江 边 踏 青 罢 , 回 首 见 旌 旗 。fēnɡ qǐ chūn chénɡ mù , ɡāo lóu ɡǔ jiǎo bēi 。风 起 春 城 暮 , 高 楼 鼓 角 悲 。
- 《絕句》.[唐].杜甫.江邊踏青罷,回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
- 译文
- 注释
- 诗评
- 赏析一
- 赏析二
- 赏析三
- 此诗为诗人 春日伤战乱之作。沿着江边踏青归来,回头望见军营的旗帜在飘动。春 风吹,成都夜幕降临,高楼上响起悲壮的鼓角声。春天本是万物竞生的 美好时节,却见“旌旗”、闻“鼓角”,战乱犹存,怎能不令诗人感到 悲伤?
- 这首短诗写的是诗人到江边游玩,享受了美好的踏青节日之后,正欲赋归,却遇上吐蕃军队入侵四川,成都戒严,一时间旌旗鼓角,弥漫春郊。阳春三月,春色满溢,本是一件极乐之事,忽然之间,战争的鼓声传开,转眼之间,从和平到战争,看来,定是要辜负这大好春色了。踏青为春日郊游,也称“踏春”,一般指初春时到郊外散步游玩。旧时曾以清明节为踏青节,不过,踏青节的日期因时因地而异,有正月八日的,也有二月二日或三月三日的,后来则以清明出游踏青居多。
绝句
陈师道
书当快意读易过,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时开?
作于元符二年(1099)困居徐州时,尽管不堪其贫,作者却不以为意,依然左右图书,欲以文学名后世。其时黄庭坚被斥逐戎州,苏轼被贬海外,张耒任职宣州,皆无因相见。时有《寄黄充》诗也说:“俗子推不去,可人费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娱!”可参读。
全诗发抒生活苦闷,纯以意为。前二各说一事,上句说心爱的书可惜容易读竟——要是总有“且待下回分解”敢情好,只是想得美!谁叫你一读起来连饭也不想吃,非一口气读竟不行。所以从古以来乐读的人对心爱的书,就存在想读完又怕读完、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态,如嵇康“每读二陆之文,(就)未尝不废书而叹,恐其卷之竟也。”
下句说性情投合的人,天天盼他来,老是盼不来——盼谁谁就来敢情好,还是想得美!没有预约,可人怎么会来?可人非神,何从知道你盼他来?即使知道你盼他来,但可能因为不得已的原因,未必来得了。此一命题的逆命题,即“俗子推不去”,也成立,但无重复必要。首句换言读书,各为一意,了不相干而又未尝无干,顿觉精警无比。
谁没读过好书,谁没有期待过可人?这两句所写,都是常人共有的生活感受,而又发常人所未发,所以叫人过目不忘,觉得作者简直是在为我写心。末二句由以上个别事例推及一般,说人生事与愿违的情况之多,往往如此,结论是难怪人生的苦恼总是多于快乐。诗的结论代表了一种认识误区。作者不明白什么是“完一美”,若要好,须是了也(“一定要有完全的休止,才纺织成完美的音乐”)。凡事都要进得去、出得来呀。作者只知道读书投入的乐趣,然而好书读竟也是一种满足呀。作者又未免太自我中心,可人不来,你为何不去呢?再说也可以打个电话约呀。何必自找烦恼呢?此东坡所以为东坡,而后山所以为后山。
本篇毕竟道出了很有意思的生活体验,固无妨其为佳作。
绝句
绝句
一种全首四句,每句五字或七字,平仄、用韵格律甚严的诗体。又称“截句”、“断句”、“绝诗”。本有占绝、律绝之分,今专指律绝。每句五字者称“五言绝句”,简称“五绝”;每句七字者称“七言绝句”,简称“七绝”。在律诗兴起的同时产生,属近体诗。明徐师曾《文体明辨》:“绝句源于乐府,下及六代,述作渐繁。唐初,稳顺声势,定为绝句。绝之为言截也,即律诗而截之也。故凡后两句对者是截前四句,前两句对者是截后四句,全篇皆对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对者是截头尾四句。故唐人绝句皆称律诗。”刘熙载《艺概·诗概》云:“绝句取径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
绝句juéjù
律诗的一种体裁,每首四句,分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
绝句jué jù
诗的一种,每首共四句,有一定的平仄格式。每句五字的叫五言绝句,每句七字的叫七言绝句:众人闻得宝琴将素习所经过的各省内的古迹为题,作了十首怀古~,内隐十物,皆说“这自然新巧”。(五十·1181)
绝句【同义】总目录
绝句小律诗
绝句
一种全首四句,每句五字或七字,平仄、用韵格律甚严的诗体。又称“截句”、“断句”、“绝诗”。本有古绝、律绝之分,今专指律绝。每句五字者称“五言绝句”,简称“五绝”; 每句七字者为“七言绝句”,简称“七绝”。在律诗兴起的同时产生,属近体诗。明·徐师曾《文体明辨》:“绝句源于乐府,下及六代,述作渐繁。唐初,稳顺声势,定为绝句。绝之为言截也,即律诗而截之也。故凡后两句对者是截前四句,前两句对者是截后四句,全篇皆对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对者是截头尾四句。故唐人绝句皆称律诗”。清·刘熙载《艺概·诗概》 中所谓“绝句取径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之说,可谓深得其中三昧。详见“五绝”、“七绝”条。
绝句
参见“律绝”条。
绝句
诗体之一,每首四句,每句五言或七言。《容斋续笔》卷八:“王荆公~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绝句
诗体名。以五言四句或七言四句构成。五绝每首20字,七绝每首28字。这种四行小诗在文学史上是较早就有的,但其诗律化,实际上与律诗一样,经过齐梁,到唐代而定型下来,成为近体格律诗中重要的一类。包括古绝和律绝两种。古绝产生于律诗之前,不讲平仄,用韵灵活,形式较为自由。律绝产生于唐代,讲究平仄,押平声韵,可用对仗,也可不对仗。参见“近体诗”条。
绝句
又称 “句绝” “断句”“句断”。古代学者用以指明文句停顿或结束的地方。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春秋左传音义·僖公二十三年》中,于“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薄而观之”条 “胁”字下注:“绝句”,于“欲观”二字下注: “如字,绝句。一读至‘裸’ 字绝句。”宋孙奕 《示儿编》卷十二: “ 《周礼宫正》: ‘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凡邦之事跸。’ 郑司农读火绝之,云 ‘禁凡邦之事跸。国有事,王当出,则宫正主禁绝行者,若今时卫士填街跸也。’ 郑康成注‘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句绝。”宋王质《诗总闻·陟岵》: ‘父曰嗟,予子行役。’ ‘嗟’断句,文势当然,语意更切。”清孙诒让《札迻》:“《庄子·天运》: ‘杀盗非杀人。’ 郭注 ‘非杀’ 句断。”
各种诗
皇帝作的诗:宸藻 天章
皇帝作的诗歌:宸歌
高僧所写之诗:雁门偈
古体诗:古(古诗;~律;~风) 辞(木兰~)
篇幅较长的古体诗:长古
诗体名:律诗
介于今体诗与古体诗之间的一种诗体:格诗(半格诗)
旧体诗:律(五~;七~) 绝(绝句;绝诗;五~;七~) 截句
词曲调牌的名称:令(小~)
七言律诗:长句
诗的一种韵文形式:词(~律;~牌;雅~;宋~) 诗余
词的别名:琴趣
短调的词:令曲
合乐的诗歌:诗乐
伴以雅乐歌唱的诗歌:雅歌 疋歌
临时感触而作的诗:即景 即兴(即兴诗)
摘取前人诗句拼成的诗:集句
经过翻译的诗歌:译诗
隐含禅理的诗:诗禅
以宫庭生活为题的诗:宫词
抒发感慨的诗:感遇诗
反映一定历史现实的诗歌:诗史
长的诗篇:长诗 长韵 长语
篇幅较长的诗歌:长歌
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长诗:史诗
用口语写的小诗:语体诗
短的诗词:小句
信口乱凑的诗:诌诗
辞意诡异、语调激切的诗:诡诗
前人遗留下来的诗歌:遗歌 遗唱 遗诗 遗篇
诗词气势奔放:怒猊抉石
251 绝句
诗体,也称截句、断句、绝诗。通常有五言、七言两种,简称五绝、七绝,也偶有六言绝句。绝句来源于汉及魏晋南北朝民歌。唐代律诗形成以前,已有绝句,亦押韵,但平仄较自由,或称古绝句。唐以后通行的近体绝句,格律相同于八句律诗中的前、后或中间四句,韵律有严格的要求。绝句这一形式灵活轻便,宜于表现生活中一瞬即逝的意念和感受,因而受到唐以后历代诗人的喜欢,创作之繁荣超过其他各种诗体。
绝句jueju
诗体名。也称截句、断句、绝诗。每首定格为四句,以五言、七言为主,简称五绝、七绝,偶有六言绝句。“绝句”名称大约起于南朝。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指出:“五言绝始汉人小诗,而盛于齐梁。七言绝起自齐梁间,至唐初四杰后始成调。”唐以前的绝句押韵平仄都较自由,或称古绝句。唐以后盛行近体绝体,格律相同于八句律诗中的前、后或中间四句。
绝句灵活轻便,适宜于表现生活中一瞬即逝的意念和感受,因而广被采用。数量之多超过了其他各体诗。宋代洪迈辑录唐人绝句至万首之多,约占现存唐诗总数的五分之一。盛唐的李白、王昌龄、晚唐的杜牧、李商隐都以绝句擅长。唐代乐府之作已不合乐,因此诗人多用绝句形式写作配乐歌唱的歌词。如王维的《渭城曲》、李白的《清平调》等。所以绝句也有唐人乐府之称。
绝句
亦称截句、断句、绝诗。每首定格为四句,以五言、七言为主,简称五绝、七绝,偶有六言绝句。“绝句”名称约起于南朝。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指出:“五言绝始汉人小诗,而盛于齐梁。七言绝起自齐梁间,至唐初四杰后始成调。”唐以前的绝句压韵平仄都较自由,或称古绝句。唐以后盛行近体绝体,格律相同于八句律诗中的前、后或中间四句。绝句灵活轻便,适宜于表现生活中一瞬即逝的意念和感受,因而广被采用。数量之多超过了其他各类诗。宋代洪迈曾辑录了唐人绝句万首之多,约占现存唐诗的五分之一。盛唐时的李白、王昌龄,晚唐的杜牧、李商隐都以绝句擅长。唐代乐府也已不合乐,因此诗人多用绝句形式写作配乐歌唱的歌词。
绝句
也称“绝诗”“截句”“断句”等,是近体诗的一种。绝句全首限定只能是四句,是一种在格式上与声律上都有着十分严格规定的诗歌形式。绝句中每句五言的称“五绝”,每句七言的称“七绝”,还有比较少见的每句六言的“六绝”。绝句要求在平仄、对仗、押韵等方面,都遵循一定的规律与原则进行创作,每句之内、句与句之间的平仄声调的调配,也都是有着一定的规格与限制的。绝句要求在每二、四句的末尾押韵,而第一句则不一定要求押韵,一般绝句的韵脚多为平声字,有时在个别情况下也用仄声字,但无论平声还是仄声,都要求必须一韵到底,中途不得换韵,也不能邻韵通押。“绝句”“截句”“断句”均有短、截之意,因此有绝句是截取律诗一半而成之说。绝句或截取律诗的首尾两联,或截取中间两联,或截取上半首,或截取下半首,但以截取首尾两联的形式最为常见。唐初还有一种只要求押韵,而不要求声律的绝句,称之为“古绝”。绝句的形式严格,音韵优美,但严格的格律限制,则有碍于表达更为丰富的思想情感与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
绝句
诗体。又称“截句”、“断句”、“绝诗”。来源于汉及魏晋南北朝歌谣,名称则大约起于南朝。每首仅四句。以五言、七言为主,简称“五绝”、“七绝”。也偶有六言绝句。梁、陈时绝句泛指四句短诗,押韵、平仄均较自由,又称“古绝句”。唐以后盛行近体,平仄、押韵均有一定规则。
绝句
诗体名。也称“绝诗”、“断句”、“截句”。每首仅有4句,以五言、七言为主,简称五绝、七绝,也偶有六言绝句,平仄和押韵都有一定规则。在唐代律诗形成之前,已有绝句,平仄较自由,后人称为“古绝句”,以和近体绝句相区别。绝句来源于魏晋南北朝歌谣,唐以后盛行近体绝句,其格律相当于律诗的前4句、后4句或中间4句,或首尾两联相组合,故后人有人认为绝句是截取律诗之半而成,这是从唐人绝句的格律形成归纳出的一种说法。绝句篇幅短小,灵活轻便,适宜表现生活中种种感情与意念,广为诗人所采用。有宋代洪迈编《唐人万首绝句》。
绝句jue ju
a poem of four lines,each containing five or seven characters,with a strict tonal pattern and rhyme scheme
绝句jue ju
regulated verse quatrains
绝句
jueju;poem with four lines to a stanza,each line consisting of five or seven characters
- 悲剧是什么意思
- 悲剧是什么意思
- 悲剧是什么意思
- 悲剧是什么意思
- 悲剧是什么意思
- 悲剧是什么意思
- 悲剧是什么意思
- 悲剧是什么意思
- 悲剧是什么意思
- 悲剧是什么意思
- 悲剧喜感是什么意思
- 悲剧心理学是什么意思
- 悲剧心理学是什么意思
- 悲剧心理学是什么意思
- 悲剧心理学是什么意思
- 悲剧性是什么意思
- 悲剧性是什么意思
- 悲剧性是什么意思
- 悲剧意识与悲剧艺术是什么意思
- 悲剧感是什么意思
- 悲剧感是什么意思
- 悲剧生涯是什么意思
- 悲剧的诞生是什么意思
- 悲剧的诞生是什么意思
- 悲剧的诞生是什么意思
- 悲剧的诞生是什么意思
- 悲剧的诞生是什么意思
- 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是什么意思
- 悲剧:秋天的神话是什么意思
- 悲号是什么意思
- 悲哀是什么意思
- 悲哀是什么意思
- 悲哀的咏叹调是什么意思
- 悲哉于嗟兮,心内切磋。是什么意思
- 悲哉秋之为气也是什么意思
- 悲哉秋之爲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是什么意思
- 悲喜交集是什么意思
- 悲喜交集是什么意思
- 悲喜交集是什么意思
- 悲器是什么意思
- 悲回风是什么意思
- 悲士不遇赋是什么意思
- 悲壮的征程是什么意思
- 悲壮的颂歌是什么意思
- 悲天悯人是什么意思
- 悲天悯人是什么意思
- 悲天悯人是什么意思
- 悲太山之爲隍兮,孰江河之可涸。是什么意思
- 悲夫黄鹄之早寡兮,七年不双。宛颈独宿兮不与众同,夜半悲鸣兮想其故雄。是什么意思
- 悲夷犹而冀进兮,心怛伤之憺憺。是什么意思
- 悲忧穷戚兮,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绎。是什么意思
- 悲怀是什么意思
- 悲怀集是什么意思
- 悲怆交响曲是什么意思
- 悲悦在人心是什么意思
- 悲悯是什么意思
- 悲情城市是什么意思
- 悲情诗人——朱湘是什么意思
- 悲惨是什么意思
- 悲惨世界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