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见欢
唐教坊曲名。后用作词牌。又名《秋夜月》、《上西楼》、《忆真妃》、《乌夜啼》。双调三十六字,上阕三平韵, 下阕两仄韵两平韵。参见“常用词谱”类。
相见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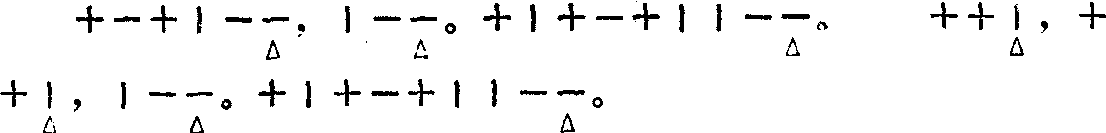
五平韵互叶,两仄韵互叶。
相见欢
唐教坊曲,用作词调。又名《秋夜月》、《上西楼》、《西楼子》、《忆真妃》、《月上瓜州》,李煜词亦题作《乌夜啼》,宋人或沿用之。唐曲《相见欢》之调名本义及源流已无考。夏敬观《词调溯源》“夹钟商”内列《秋夜月》,云“一名《相见欢》,见《教坊记》”,然由唐至宋之演变关系已不可考。李煜《乌夜啼》共三首,实为两体,其中“昨夜风兼雨”一首为四十七字体,欧阳修词名《圣无忧》,赵令畴词名《锦堂春》;其中“林花谢了春红”及“无言独上西楼”二首为三十六字体,即《相见欢》。《词律》卷二以李煜所作(无言独上西楼)为正体,并云:“按此调本唐腔,薛昭蕴一首正名《相见欢》,宋人则名为《乌夜啼》,而《锦堂春》亦名《乌夜啼》,因致传讹不少。”《词谱》卷三以薛昭蕴所作(罗襦绣袂香红)为正体,格律同李煜所作,双调,三十六字,上片三句三平韵,下片四句二平韵,换头错叶二仄韵,后人所作亦多如此。《词谱》列别体四种。
相见欢
落花如梦凄迷,麝烟微,又是夕阳潜下小楼西。
愁无限,消瘦尽,有谁知? 闲教玉笼鹦鹉念郎诗。
写小说者很注意通过描写人物外部细微动作,刻画人物心理,纳兰性德的词也擅长运用这种手法,细致地表现抒情主人公心灵深层的微妙情绪,上面这首小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首词写楼头思妇的愁闷。落花如梦,春天过去了; 夕阳西下,一天又过去了。佳人见落花而有“如梦”“凄迷”之感,透露出她的伤春情绪。“麝烟微”,显然她一直孤独地等待着,熏炉中袅袅香烟已经燃尽,表明等待的时间已经很长很长了。“夕阳西下”,而曰“又是”,表明她是日复一日地等待。正因为她镇日心思重重,所以感到夕阳是“潜下”西天,表现出抒情主人公无可奈何的落寞情绪。
上阕刻画一个含愁脉脉的思妇形象。下阕过片三句承接上面的意脉,进一步渲染她的愁情。“愁无限”,因内心有无限之愁,“消瘦尽”,形体上也憔悴不堪,“有谁知?” 一句问语,吐出了她心中无限幽怨! 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闲教玉笼鹦鹉念郎诗”,突出写一个教鹦鹉念诗的细节,把思妇的心情和盘托出,原来她一直在等待、思念的人,是她的“郎” 远行在外的丈夫。封建社会的妇女,不能离开绣阁朱户,便只好调弄和她一样被关闭在富丽堂皇的玉笼中的鹦鹉,可见其内心是十分凄凉寂寞的。而她教导鹦鹉学舌,念的又都是丈夫的诗句,这既是消遣,又是怀念,极其生动细腻地表现出金闺少妇的心理状态。
从整首词来看,前面写落花、夕阳及人的消瘦,是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意境,而最后一笔,这一典型细节的描写,顿使全篇光采焕发,饶有韵味,并使词意具有丰富的内涵。可见这种细微动作的描写对于纯粹抒情的诗歌也是颇有意义的。纳兰词中类似的写法较多,如其《鹧鸪天》上阕云:“背立盈盈故作羞,手挼梅蕊打肩头,欲将离恨寻郎说,待得郎归恨却休。”这是写出远门的丈夫回到家中时,妻子嗔喜参半的娇态,虽然“手挼梅蕊打肩头” 句化用唐末无名氏《菩萨蛮》(牡丹含露真珠颗)的情节,但它和“背立盈盈故作羞”的情态连在一起,就活画出少妇此时特有的心态,丈夫去得太久,几乎把她忘记了,使她作恼; 但他终于盼回来了,又使她高兴,一肚子的怨气也就消了,所以“背立盈盈故作羞”,是装作不理睬的姿势,手挼梅蕊打他的肩头,更写出了少妇假作气恼的模样,而这种人物外形、动作的描写,和写情血肉相连,将思妇内心酸甜苦辣滋味曲曲传出。纳兰性德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很高妙。也许不无受到明清小说的影响吧。
相见欢
云闲晚溜琅琅。泛炉香。一段斜川松菊瘦而芳。
人如鹄,琴如玉,月如霜。一曲清商人物两相忘。
这首小令仅有三十六字,却创造出一个耐人留连品味的境界。这个境界的主要审美特征,只是一个字:清。泉水清澈,月光清冽,其清在色,清与浊相对。水流琅琅,琴质如玉,其清在声,清与杂相对。青松挺立,黄菊离披,其清在骨,清瘦与肥腻相对。炉香袅袅,菊香沁人,其清在气,清淡与甜俗相对。总之,词中意象,无一不清。外在的清景与无机心、无名利之想的人的心灵,内外相映,遂觉冰心玉壶,表里澄澈。
清境之中,词人又用点示性笔墨,借千古隐逸之祖陶渊明为诗境点缀。“一段斜川松菊”,似用典非用典,稍稍提掇,韵致得来不觉。陶渊明曾“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并有诗纪其事。这里提及斜川,一是因为眼前挚友相聚,情趣不减当年陶氏之游;但更重要的是斜川是与陶渊明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提及斜川,就能唤起对陶渊明清旷高古的精神风貌的感知。陶渊明多次咏叹过松与菊。《和郭主簿》其二云:“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这种高洁的风致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萧闲心境,是作者心折和读者熟悉的,稍加点示,便如轩窗洞开,清风洒然,不期而至。
和多数词作不同,这首词里几乎没有什么抒情的字眼,纯乎写景。作者没有表示对扰扰红尘、名缰利锁的厌倦,也没有表述自己的耿介独立、隐居避世之志,只是淡墨白描,绘出一幅清景,却使人自觉其中乃陶渊明、林和靖一类人物。闲云松菊,非象征也非寄托,而其中自有意趣。
相见欢
【题 解】
全诗写的是亡国之君囚禁生活的所见所感:环境的束缚,生活的寂寞,愁思的别味,难以明言。
【注释翻译】
鉴赏分析
全篇词情凄婉,哀怨欲绝。上下阕分别以“寂寞”、“离愁”为中心,前为因后为果,前后照应,倍显悲凉、冷清与无奈。
上阕写景,勾勒出作者孤独寂寞的身影,用新月、梧桐、深院、清秋这些景物渲染了凄凉幽美的环境。一个“锁”字暗示了作者被囚的处境,院是“深”的,月是弯的,梧桐是“寂寞”的,人是“独”的、是“无言”的,语言通俗明白而又十分精练准确。李后主愁恨满怀、踽踽独上高楼的形象跃然纸上。上阕景中有情,情溢景外。
下阕转为抒情,用了形象生动的比喻和细致入微的刻画,使得抽象的感情切实可感,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作者用有形之丝比喻无形之愁,“剪不断,理还乱” 以重笔直抒胸臆,比喻愁绪多端、愁情缠绵。他的离愁,不是一般的男女离别之愁,而是失掉故国的深愁长恨;他的思如丝,越剪头绪越多,越理愁思越浓,可谓“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表现了词人欲哭无泪、欲罢不能的悲极情态。此所谓“无声胜有声”,此种无言之哀,更胜于痛哭流涕之哀。
《相见欢》
《相见欢》
朱敦儒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中原乱,簪缨散①,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②,过扬州。
【注释】 ①簪缨: 簪是用来连结头发和帽子的长针,缨是帽带,这里的簪缨代指贵族。②倩: 请。
【词大意】 我登上金陵城的西楼,看到的只是一片萧瑟的清秋景象; 万里迷茫的夕阳余光洒满大地,伴唱着呜咽似泣的江流。金兵踏破中原,人民流离失散,不知几时收?呼啸的悲风啊! 请把我的泪水,吹送过扬州。
【赏析】 朱敦儒这首词,是他南渡后登金陵 (今江苏省南京市)城上西楼眺远时所写的。词表现了他忧虑国家前途,怀念故土的爱国情怀。词的构思精巧,韵律自然和协,感情激越动人。
上片写景,多用暗喻和双关语,着意在借景抒情,但又不同于同类借景抒情的词作,而在抒情上更加强烈。开头两句,写词人登楼眺远,触景生情,引起无限感慨。第一句是作地点、登楼眺远的交代。金陵城上的西门楼,居高临下,面向波涛滚滚的长江,是观览江面变化,远眺城外景色的绝妙去处。古来不少文人骚客,曾登临此楼,抒发胸襟,留下不少流传千古的名篇。由于时代的变迁,人物各异,他们所抒发的感慨也各不相同。譬如,李白的 《金陵西楼月下吟》诗,抒发的是对南齐诗人谢朓的缅怀。朱敦儒这首登楼抒怀之作,既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为区区个人之事,而是感叹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
第二句“倚清秋”,即触景生情,进入主题。“清秋”二字,词意双关,既指深秋季节,又指秋色萧条的景象。但它又偏重于后者。“清秋”,容易引起人们产生凄凉的感受。宋玉的 《九辩》 开头就写道: “悲哉! 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应当说,宋玉是悲秋之祖了。朱敦儒这句词的悲秋,含意较深,是暗喻山河残破,充满萧条气象。而 “倚清秋”的 “倚”字,用得与众不同。一般用于倚栏或倚楼。词人把“倚”字用在 “清秋”前,即变成倚靠清秋了。“清秋” 自然无法倚靠,这是象征手法。显然,这“倚” 字,就有陪伴之意,立意较新,意境奇妙。
三、四两句,进一步用暗喻手法,描写 “清秋”傍晚的凄凉景象。可能心情愉快的人,会描写 “夕阳无限好”,金光洒满大地; 江水滔滔,奔腾向前的美好意境。然而,词人并没有心绪欣赏这样的自然景色,他是用“万里夕阳垂地” 来暗喻祖国山河破碎而呈现出的一种迷茫气象。“大江流”一句,是用好似呜咽哭泣之声的江中流水,来反映词人悲凉、沉痛和抑郁的心境。
下片抒情,用直抒胸臆的方式,来表达词人的亡国之痛,及其渴望收复中原的急不可待的心情。“中原乱”三句,既是对北宋灭亡、山河残破、人民流离的景象的辛酸回忆;又是对主和派阻挠抗金斗争的愤懑,并提出何时才能收复中原的质问。“簪缨散” 是比喻句,象征官僚和贵族纷纷南逃。“几时收”,这里表现两层意思,一是反映词人渴望收复中原的焦急心情,二是对朝廷不图恢复的指责。两者中又偏重于后者。
最后两句,是用拟人化的手法,表现词人的亡国之痛及其对中原故土的怀念深情。作者在另一首同样主题的《采桑子·彭浪矶》词中写道:“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这种直陈其事的写法,显得太露,没有这两句含蓄而有意境。伤心流泪,已经能说明人的痛苦了,但词人却写“悲风吹泪,过扬州”,把眼泪送到沦陷区,这就更加表现了词人悲愤交集、痛苦欲绝的感情。所以“悲风吹泪”四字,用得极好。风本来没有感情,风前冠一“悲”字,就给“风”注入了浓厚的感情色彩。“试倩”,是请托的意思,是拟人化手法。不难看到,这两句是词人爱国思想发展到高潮而产生的名句,它铿锵有力地结束了全词,显示出了本首词所具有的光彩。
相见欢
李煜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诗词创作如果仅局限于具体事情,满足于吟风弄月,意义是不大的。李后主词的一个显著的优长便是善于从小小题材中提炼出重大的主题,赋予风花水月以象征意蕴,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这首《相见欢》便是很突出的作品。
在上片里,后主将一已亡国的哀痛转化为对自然界花木的盛衰的慨叹。“林花谢了春红”与北宋晏殊《破阵子》“荷花落尽红英”句法略同但韵味迥别。“红英”便是“荷花”的同义反复;而“春红”则是春天的红色,生命与青春的象征,写来就多一层意蕴,比一般地写落花要令人心惊,使人联想到同一作者“只是朱颜改”的名句。于是“太匆匆”的一叹尤见沉重,似乎是对春天的抱怨。花谢是无可更改的自然规律,可怨只在这一切来得太快,出人意表。其所以如此,乃是外来摧残的缘故:“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这个九字长句,意思与赵佶《燕山亭》:“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辛弃疾《水龙吟》:“可惜流年,忧愁风雨”相同。将“风”、“雨”分属“朝”、“晚”是互文,能增添一重风雨相继、无休无止的意味。通过这样的对比,最易看出后主在铸词造句上的功夫。
下片从自然界生命的盛衰感慨转入对人生无常的感慨。过渡极其自然。“胭脂泪”三字是春花与美人的泯合。“胭脂”承“春红”而来,“泪”承“风雨”而来。可见上文“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不仅有风雨落花的含意,同时也兼关岁月催人之意。于是只有借酒浇愁。有人认为“胭脂泪,留人醉”意言亡国的当初宫人哭送情事,虽无不可,却不必然,似更具一般叹惋人生的色彩。“几时重?”这一问更进一步,春花谢了还会重开,而失去的青春与欢娱,是永不重来。此即所谓“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所以词人最后归结到人生无常这一普通规律上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一句与作者《虞美人》“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在明喻上极为相似,但在音情上别饶顿挫。叶嘉莹细致的辨析道:《虞美人》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九字,乃是承接上句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愁”在上句,“水”在下句,因此下一句就是一个单纯的象喻而已,九个字一气而下,中间更无顿挫转折之处;而此词末句把“恨”隐比作“水”,前六字写“恨”,后三字写“水”,因此“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九字形成了一种二、四、三之顿挫的音节,有一波三折之感。如果以自然奔放而言,则《虞美人》之结句似较胜,但如果以奔放中仍有沉郁顿挫之致而言,则《相见欢》之结句似较胜。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后主词大都萦回着一种恋旧伤逝情绪,这种情绪,经受过人世挫折的人皆有之,可说是一种极普遍的情绪。这首词中“无言独上西楼”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以及中夜梦回听“帘外雨潺潺”的“客”者、面对“春花秋月”之景哀怨难排的愁人……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美好过去的痛悼与忏悔。
词人虽然有着帝王身份,却并不过多涉及具体情事,而是常将一己的深哀巨痛与普遍的人生感慨结合,这是后主词表情上一大特色。即如《梦江南》点出“游上苑”,而“车如流水马如龙”的风月繁华之事,也是具有普遍性的经验。而此词中的抒情主人公的身份,也并不是确定的。词人经常的作法是,或将个人特有的哀痛,与宇宙人生的哲理感喟融为一体,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或用模糊语言,说明而不说尽,留下未定与空白,让读者用自身经验去填补,如此词的“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只说别是一般滋味,不说别是什么滋味,让人低回深思。
后主诃虽然反复歌咏一个主题,却毫无雷同之感,而令人百读不厌,这与他语言和造境的独创性分不开。如比喻这种最通常的修辞手法,在此词中便别开生面。“心乱如麻”,乃是极平常的比喻,然而到后主笔下,变得多么富于艺术魅力啊!究其所以然,盖在比喻四要素(喻体——麻,本体——心,喻诃——如,共通特性——乱),通常是不能省略喻体的。而此词恰恰省去这个“麻”,而用“剪不断,理还乱”,将一团乱麻的意念活脱脱表达出来。一个漂亮的、独出心裁的比喻,照亮了全部词境。
后主词潜伏着一种低回唱叹的情韵,这与长短错综的形式的创用大有关系。词人注意形式对抒情的巨大作用,在词中成功地将短而急促和长而连续的两种句式妥贴地安排在一起,来表现沉郁复杂的情感。其词中九字句常常出现在三字句之后,如此词的“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及别一诃的“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种长短错综的音调来表达莫可名状的惆怅,真有长吁短叹之妙。
相见欢
李煜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此词写伤别,却从春花匆匆凋谢落笔,既有诗情画意,又传惊叹之神。以花喻人,点朝雨晚风的深层内涵。下片承上写人,以“胭脂泪”明身份,描摹情态。“留人”又双关。“醉”字极写相别难堪之情,如狂如痴。“几时重”虽问无疑,以花谢喻再逢之难。以议论结,道出伤别生恨词旨。“无奈”“自是”深化词义:尤能揭出人生苦闷之底蕴,力重千钧。
相见欢
李煜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词以离愁鸣亡国之音,哀惋凄切。起句直绘愁态。接写愁境:仰望新月如钩,俯视桐阴深锁,仰俯之间,百感交集。下片抒情,谓千丝万缕之愁不可剪,不可理,正写出别是一般滋味之愁的特殊个性。昔日花天酒地的南朝之主,变成北地幽囚,这愁滋味自然与众不同。
相见欢
朱敦儒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
该词作于靖康之乱以后。词人登楼远眺,感慨系之,对中原故土的怀恋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进发为激越之情。上片以秋气夕阳写山河破碎,下片仰问茫茫苍天,直抒胸臆。最后以悲风洒泪作结,感情炽热真切,深沉凝重。
相见欢
〈隐〉清末以来邮递业指邮递员。
相见欢xiāng jiàn huān
❶旧时邮政业谓送信人。《切口·信局业》:“相见欢: 送信之人也。”
❷旧时药行业谓夜合花。《切口·药行业》:“相见欢: 夜合花也。”
相见欢
词牌名。又名《秋夜月》、《上西楼》、《西楼子》、《月上瓜洲》、《乌夜啼》、《忆真妃》。原为唐教坊曲名,后用作词牌。双调。清·万树《词律》:“此调本唐腔,薛绍蕴一首正名《相见欢》。”始见于《花间集》薛绍蕴词。
全词上下两片,共七句三十六字。上片第一、二、三句皆用平声韵; 下片第一、二句押仄声韵,第三、四句换平声韵。上下片两结句均为九字句,亦可于第四字或第六字略停顿,但句法须蝉联不断。常用格体为:
(平)平(仄)仄平平 (韵),仄平平 (韵)。(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韵)。
(仄)(平)仄 (换仄),(仄)(平)仄(韵),仄平平 (换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相见欢
一名 《乌夜啼》,南唐后主李煜后期重要代表作品,全词是这样: “无言独上高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深邃聊寂的院落,梧桐在秋风中瑟瑟作响,一弯冷月高挂星空,清辉照在旷寂的院里,映出了梧桐叶斑驳的阴影,在这令人发瘆的夜晚,一位不眠的囚徒,踽踽独行,登上了高楼……这就是词上片所描绘的一幅冷落凄凉的画面。这里作者是在写景,也是在写情; 作者正是通过对景物细致人微的刻画,把难以名状的深愁重恨揭示出来,而一个 “锁” 字,是既写自然环境为肃杀之秋气所笼罩,也是在暗寓自身被重门深宅所幽禁,明写暗喻,堪为传神之笔。而对撩人愁怀的景物,伴随着的是无穷无尽的离恨别愁; 愁恨纷繁,万感萦怀,欲剪不断,想理又乱,这是下片紧接上片因景而抒情的情愫。离恨别愁,虽有千丝万缕,未必不可剪,不可理,此处所言 “剪不断,理还乱”,则作者心情的凄怆与缭乱可想而知。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句,出语似乎平淡无奇,但却把非身历其境者所能品尝的难言苦痛婉曲深致地传达给读者,其艺术上的效果,甚于呼天抢地、号啕流涕的描写。《相见欢》所表达的情感就是如此至哀至痛,故被后人称为 “最凄惋” 的 “亡国之音” (见《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
- 菱形紋銅尺是什么意思
- 菱形纹铜尺是什么意思
- 菱形纹陶罐是什么意思
- 菱形缩栉蚤是什么意思
- 菱形翼型是什么意思
- 菱形肌是什么意思
- 菱形肌肌力试验是什么意思
- 菱形花纹加工是什么意思
- 菱形贴毛绢是什么意思
- 菱形队形是什么意思
- 菱形面是什么意思
- 菱暖紫鳞跳复没,柳阴黄鸟啭还飞。是什么意思
- 菱枣是什么意思
- 菱格因缘故事图壁画是什么意思
- 菱格因缘故事图(局部)壁画是什么意思
- 菱格山野图壁画是什么意思
- 菱格本生和因缘故事图壁画.是什么意思
- 菱格本生故事图壁画是什么意思
- 菱格本生故事图(大施抒海)壁画是什么意思
- 菱格本生故事图(局部)壁画是什么意思
- 菱格连弧纹彩陶罐是什么意思
- 菱桶是什么意思
- 菱棹是什么意思
- 菱歌是什么意思
- 菱歌谁伴西湖醉。是什么意思
- 菱歌面面来渔鼓,灯火层层到客舟。是什么意思
- 菱水是什么意思
- 菱汀系带,荷塘倚扇。是什么意思
- 菱江集杂曲是什么意思
- 菱沸石是什么意思
- 菱洲是什么意思
- 菱浦是什么意思
- 菱湖是什么意思
- 菱湖三女史集是什么意思
- 菱湖公园是什么意思
- 菱湖有馀翠,茗圃无荒畴。是什么意思
- 菱湖白扁豆是什么意思
- 菱湖鎮金石志是什么意思
- 菱溪草堂是什么意思
- 菱溪诗话是什么意思
- 菱溪遗草是什么意思
- 菱熟经时雨,蒲荒八月天。是什么意思
- 菱生山中是什么意思
- 菱科是什么意思
- 菱窠是什么意思
- 菱米是什么意思
- 菱粉是什么意思
- 菱粉糕是什么意思
- 菱紫叶蝉是什么意思
- 菱纹叶蝉是什么意思
- 菱纹罗是什么意思
- 菱舟是什么意思
- 菱舫是什么意思
- 菱船是什么意思
- 菱芋藩篱下,渔樵耳目前。是什么意思
- 菱花是什么意思
- 菱花似月嫌双笑,柳叶无风爱独摇。是什么意思
- 菱花形仙人镜是什么意思
- 菱花形单龙镜是什么意思
- 菱花形宝相镜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