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鼓
《诗经·邶风》篇名。此诗反映远征战士长期不得归家的怨愤情绪。《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参以《左传》有关记载,郑玄以为这是描写鲁隐公四年(前719),卫与宋、陈、蔡联合伐郑的战争(《毛诗传笺》)。也有人以为是写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宋伐陈,卫穆公出兵救陈的战争。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全诗五章,章四句。突出描写士兵远征于外,处境艰险,情绪极度消沉,“一时怨愤离叛之状可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与普通征人思乡的诗不尽相同。
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①土国城漕,我独南行。②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③不我以归,忧心有忡。④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⑤于以求之?于林之下。⑥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⑧于嗟洵兮,不我信兮。⑨
【注释】 ①镗(tang堂):鼓声。踊跃:形容演武时跳跃击刺的动作。兵:武器。②土、城:皆用作动词,修筑城池。漕:卫邑名,今河南滑县东南。③孙子仲:卫国军队的统帅。“孙”是姓氏,字子仲。孙氏是卫国的世卿。平:平定。崔述《读风偶识》:“凡两国不相和而为和之,曰‘平’。”一说联合。④以:犹“与”。有忡(chong 冲):犹“忡忡”,忧愁不宁的样子。⑤爰:于何,在哪里。⑥于以:也是“于何”的意思。⑦契:合。阔:疏。“契阔”这里用作偏义复词,偏用“契”义,言不论生死都要在一起。成说:立下誓言。⑧于嗟:叹词。活:犹“佸(huo)”,相会。⑨洵:久远。
【译文】 擂起军鼓咚咚响,踊跃劈刺练刀枪。筑土墙,修漕城,我独从军向南行。跟着统帅孙子仲,平定纠纷陈与宋。别人回家我没分,心悲意苦愁重重。哪里停留哪里住?我的战马死何处?什么地方来找我?山林之下收白骨。“不论生死在一起”,山盟海誓对你许。紧紧拉住你的手,与你偕老到白头。我们相隔太遥远,要想重逢难上难。我们分别太久远,昔时誓语成空言。
【集评】 《毛诗序》:“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
清·姚际恒:“《小序》谓‘怨州吁。’郑氏以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按此事与经不合者六。……按此乃卫穆公背清丘之盟救陈,为宋所伐,平陈、宋之难,数兴军旅,其下怨而作此诗也。”(《诗经通论》卷三)
清·方玉润:“细玩诗意,乃戍卒嗟怨之辞,非军行劳苦之诗。当是救陈后晋、宋讨卫之时,不能不戍兵防隘,久而不归,故至嗟怨,发为诗歌。”(《诗经原始》卷三)。
【总案】 《诗序》认为这首诗是卫州吁于鲁隐公四年(前719年)联合陈、宋、蔡三国伐郑时,士卒嗟怨之作。清代不少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那次战争时间很短,而且州吁回国不久就中了卫国老臣石碏的计策,被陈侯诱杀,诗中所云“不我以归”等等与这段史实不符。所以姚际恒等提出此诗实是描写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卫穆公出兵干涉陈宋两国战争的史事。其实,正如方玉润所说:“此戍卒思归不得诗也,又何必沾沾据一时一事以实之哉?”(《诗经原始》)春秋期间,各诸侯国之间征战频繁,百姓不堪其苦,而从军士兵于饱受战乱之苦之上又加以去家离亲之痛。《诗经》中抒写战争的诗篇很多,其中既有战士们同仇敌忾的高歌,也有士兵对穷兵黩武的怨恨和对故国亲人的思念。但是,像本篇如此情绪低落消沉,语气悲观绝望的诗作则可称绝无仅有。全诗纯用赋体娓娓叙来,尤见沉痛。
击鼓
诗经·邶风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 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 不我信兮!
这是《诗经·邶风》里的一篇,作者是卫国与陈、宋两国共同讨伐郑国一仗中的士兵。诗中充分流露出厌战恋家的心理和情绪,缠绵婉转,痛不欲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古老的一篇士兵写战争和爱情的诗的。《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是符合事实的,代有定论。不过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决不是仅仅“怨其勇而无礼也”,而是在对不义之战的鞭挞之中,强烈地歌颂了纯贞的爱情。
诗分五章。第一章描写了战争的契机:击鼓其镗,踊跃用兵。
镗,象声词,击鼓声。兵,武器,“用兵”即打仗。战鼓擂得咚咚作响,士兵们欢呼跳跃,挥刀舞剑去打仗。乍看之下,热闹非凡,丝毫没有非战的意思。然而在这热闹的背景上,究竟隐伏着什么呢?王闿运的《湘绮楼说诗》评之云:“开口便如灞上、棘门之军,徒儿戏耳。”宋吕祖谦在其《家塾读书记》中也引过曾巩的话说:“镗然击鼓,踊跃用兵,想见州吁好兵喜斗之状。”诚然都是很尖锐的。作为一国之主的州吁竟把战争视如“儿戏”,军纪不整,行兵哗然,而且“好兵喜斗”,难怪他好景不长。“好兵喜斗”正是州吁发动不义战争的契机,热闹之中却潜伏着失败的祸机。这两句既包含了诗人的讽刺和嘲弄,又为下文的厌战与恋家张本。
“土国城漕,我独南行”。土,动词,意即加土,巩固;国,国都,即朝歌。城,筑城;漕,卫地名,即今之滑县。“南行”,朝歌,在今淇县东北,郑国在今新郑以北,由淇到新郑正是南行。这两句说,有的在朝歌加固工事,有的在漕地筑城;而我却偏偏被派在南征的行列中。上句是客,下句是主,用上句来陪衬下句。由此可见,他宁可在本国服劳役,因为那有一种安全感和亲切感;而不愿去城国打仗,因为那有一种危险感和生疏感。一个“独”字,既表达了作者的怨望之情,又体现他集天下忧患于一身的觉醒意识,更为后文夫妻不能白头偕老的主题做了铺垫。
第二章承“南行”而来,写对战争的预料。“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两句介绍“南行”的任务。从,跟随;孙子仲,即公孙子仲,此次“南行”的将帅。平,联合;“平陈与宋”即联合陈、宋和蔡三国去攻打郑国,事见《左传·隐公四年》。以下两句写对自己前程的顾虑。战争是残酷的,更何况是非正义的战争,注定是要失败的。远见卓识的诗人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说“不我以归”。“不我以归”就是“不我归”,“我不归”,用现代的话说即“我回不来了”。参战的人“朝行出攻,暮不夜归”,岂不意味着死了! 明知要战死他国,一去不返,难免“忧心有忡”。忡,忧虑不安的样子。忧虑什么呢? 以下两章便是其具体内容:
爰居爰处? 爰丧其马? 于以求之? 于林之下。
爰,句首助词,无义;居,信息;处,驻扎。丧,死伤。“于以”,在何处;之,代词,指马,也暗指人。这是第三章,是忧虑战事和自己的具体形象。“爰居爰处”,是行军驻扎,休息整顿,说的是在陈国和宋国;“爰丧其马”,战马的死伤,只能是在战场上,“野战格斗死,驽马徘徊鸣”(《战城南》)也正说的是同一境况。这是作者想象发生在郑国的事情。马死了,人也保不准死了。所以说:“你到哪里去找我啊?就到林木底下去吧!”这同“索我于枯鱼之肆”的说法何其相同!《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谓秦师伐郑,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又哭其子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师之入也。”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都是推测逆料的说法。可见我们的诗人,也同蹇叔一样地具有过人之见和忧患意识。纵观诗意,与《左传》文情事句法语气尽相同,可以断定,这也是诀别之辞,而且百般凄惨,摧人肺腑。王肃早就认为“以下三章卫人从军者与其家室诀别之辞”,这是很有见地的。
《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军败于邲,赵旃弃车而逃到林子里。逢大夫与二子乘车逃,让他们不要回头。没想到他们回头说:“赵老头在后边。”逢大怒,让他的儿子下车,并指着一棵树木说:“我到这里来收你们的尸首。”便让赵旃坐车逃掉了。第二天来寻,果然两个儿子在那树下叠尸而死。所以诗中说“于以求之? 于林之下”,恐怕不是泛泛而说的。
既然是与家室(妻子)诀别,而且是生离死别,不由得泛起一阵美好的回忆和对幸福的珍惜来。可以说第四章的忧心是由分别引发了美好的回忆,回忆又加重了忧虑的程度。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契阔”,即絜括,胡承拱云:“死生契阔,言死生相于结合,不相离弃。”子,你,此系指诗人的妻子;“成说”即说成,说好,所谓男女之间的海誓山盟。这两句是倒装,正常的顺序该是“与子成说,死生契阔”。后一句当是成说的内容:同生共死,永不分离。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执,握着。“偕老”,共同到老。我握着你的手啊,这当是原初与你恩恩爱爱“与子成说”时的情态,那有多么亲密啊。同你白头偕老,这又是“成说”的内容了。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不妨把这四句重新组合一下,以期恢复它的原貌: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诗中倒装,决不仅仅是因为修辞和押韵的需要,因为第四章是回忆,是在心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的回忆,就必然是片段的,零碎的,交叉的,作者正是惟妙惟肖地表现了这一曲折复杂的心理活动,不得不使人叹为妙笔。再者把“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放在首尾,在音乐处理上势必会得到一种突出和强调。果真如此,在以后绵亘的文学史和绮丽的爱情史上,它们竟成了不二的誓词和美好的祝愿,为我们的生活和艺术增添了不知几多奇葩和佳话。我们怎能不感谢这位失去了名姓的伟大诗人!
对未来的逆料,对往日的回忆,尽管他“忧心有忡”,也改变不了他“不我以归”的命运。人在真情大恸,无可奈何之际,未尝不呼天抢地,他也只能弹下那不该轻弹的泪。请听那撕裂肝肠的哭喊: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活,通会,会即相会的意思。洵,通悬,即生死悬绝的意思。信,通伸,即志愿的实现。其大意是:啊呀,就要远别啊!我们不能再相会啦!啊呀,生死路隔啊! 我们的誓言难实现啦!这一章与上章珠联璧合,声气相通。他要“信”的正是“成说”,而今就要死于“林之下”,哪里还能白头“偕老”!读到这里,诗人与爱妻抱头痛哭,惨不欲生的情状跃然纸上,有情读者,谁不为这一对恩爱夫妻洒一把同情之泪! 谁又不欲将发动这场战争、拆散鸳鸯的州吁扒其皮而烹其肉呢! 正因为情真意切,才感人至深!
本诗前边热闹,后边凄惨,形成鲜明对比,对爱情的歌颂和战争的鞭挞张力极大。尤其是末章“兮”字的重叠运用,使读者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如睹其人,大肆渲染,荡气回肠。
《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
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诗经·邶风》
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个被迫出征、久戍不归的卫国士兵。根据诗歌第二章中“从孙子仲,平陈与宋”(跟随统帅孙子仲,平定陈国与宋国之间的纠纷)的诗句,对本诗的写作背景可以有一定的了解。《毛诗序》: “《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州吁是在公元前719年袭杀其兄卫桓公而自立为卫君的。在他统治卫国的半年多时间中,曾两次联合宋、陈等国攻打郑国。如果《序》说成立,那么此诗即为卫君州吁伐郑时的作品。然而,清人姚际恒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此乃卫穆公背清丘之盟救陈,为宋所伐,平陈、宋之难,数兴军旅,其下怨之而作此诗也。”卫穆公平定陈、宋间纠纷,事在公元前597年。究竟《击鼓》反映的是哪次战争?方玉润的见解值得赞赏:“细玩诗意,乃戍卒嗟怨之辞,非军行劳苦之诗,又何必沾沾,据一时一事以实之哉。”(《诗经原始》)理会诗意才是第一要旨,至于背景史实作为参考也就是了。
“国风”多比兴,而本诗却没有一个比兴,全用赋法。诗歌以第一人称的“我”进行叙述。第一、二章简括地讲说了他的从军南征和留驻不归:“土国城漕,我独南行。刀“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国人运土建漕城,我独从军到南方。常驻边地不能归,满腹忧愁心痛伤。到了第三章,诗人的诉述变得细致具体了:远征队伍刚一息脚,士兵们就四散躺倒,连战马都因无人看管而丢失了(“爰”,于是,在这里。 “居”、 “处”,停下、休息)。上哪儿去找啊?竟然跑到丛林深处的大树下去了。生动的细节,真切地反映了这支队伍纪律松弛、军心涣散的状况。第四章与妻子生离时“死生契阔(聚合不离)”, “与子(指妻)偕老”, “成说”(盟约)的追忆,是何等地情深意切。然而,现实又是多么地残酷无情,他的热血和生命只能消耗在这异域他乡,誓约很难有实现的希望。强烈的不可遏止的思念和忧愤,使这位战士的诉说,终于变为痛苦的呼号:“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久远)兮,不我信(守约)兮! ”——哎呀,相隔千里遥呵,绝望没法活呵!哎呀,分离太久远呵,誓言难实现呵!
陈子展先生评论本诗,说“这是最古的一篇以兵写兵的短诗杰作。”(《国风选译》)不为过誉。
击鼓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 爰丧其马? 于以求之? 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本篇写兵士长期征伐异国,思归不得,而对统治者怨愤不满。
本篇共分五章。
诗一开头,就直接描写军队出征前的情景:“击鼓其镗,踊跃用兵。”此写:军队出征前,以击鼓作进军信号。此时,士卒们纷纷挥动刀枪,操练击杀冲刺,以显示军威。可是有些人却在“土国城漕”。既击鼓进军、操练击刺,又修工事与筑城,这就描写出战前备战的繁忙情景,烘托出战前的紧张气氛,从而交代出进军的背景。在此情况之下,点出主人公“我独南行”。“南行”,指出兵往陈宋。这两国在卫国之南。在国内修工事、筑城并非不劳苦,但他们却无需出国征战而无战死之忧,而出征兵士纵然欲“土国城漕”犹不可得。一个“独”字突出他与“土国城漕”者不同的处境与对出国南征的不满,并透露出危死之忧。此句始以直接抒情,表露对统治者不满。首章的战鼓雷鸣、兵士以刀枪击刺的紧张气氛,为二、三、四章兵士的诉苦作了渲染与設下铺垫。(以上为第一章)
紧接着交代军队 “南行”的原因: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孙子仲,当是军队的统帅,其他无考。“陈与宋”,均在今河南省境内。此次出征是跟随统帅孙子仲讨伐平定陈与宋。这就点出此次战役的非正义性。本来就不愿参加这非正义的战争,再加上长期征戍在异国,就必然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平定陈宋战役已打过很久了,为何至今还守在此,而不让我们这些幸存者返回家乡?这就引起他们忧虑不安。前两句是以叙述交代“南行”的原因,对平定陈宋战役的情景未详写,仅一带而过。这固然为篇幅所限,更是因为紧扣题旨,重在写兵士征战之苦及对久戍不得归的怨愤,战役详情无必要赘述。这是进一步直截了当表达对统治者的不满,其厌战心情已显然可见。(以上为第二章)
继而,向前推进一层,深入地陈述战争环境的艰苦与军纪松散: “爰居爰处?”此言:我们住在哪里?歇在哪里?这固然表明兵士由于无有固定安身之处,战争环境艰苦,但更表明 “军士散居无复纪律”( 《集疏》)。因而导致 “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此言: 战马跑到哪里去了?我们到哪里去找它?结果却在树林中找到了。这就以兵士散居与失马寻马两事件事,生动形象地描写出兵士久戍异国,军心涣散、士无斗志的厌战情景。人民反对非正义战争,由此再见一斑。(以上为第三章)
由于厌战,就必然更思家思妻,这就引起他回忆当初出征前与妻子话别的情景: “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临别时,我拉着你的手,与你立下誓言: 同生死、共聚散,白头同过到老。可是如今,虽然“信誓旦旦”,却难得实现。这是用倒叙笔法,追叙当初离别的情景,从侧面描写兵士不得归的忧伤及对统治者的怨恨。立誓的场面与如今的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最能感动读者的心怀。(以上为第四章)
最后,抚今追昔:“于嗟阔今,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此言:唉!我们这些离别家乡的兵士,恐怕不能活着回去了,长期离别,当年的誓约难以守信实现。诗人借沉痛的哀叹,充分倾泄兵士对自己处境的悲哀忧伤,对统治者的怨恨愤慨,更进一步反映出对非正义战争的厌弃与反抗。这是血泪的控诉。兵士最后的结果究竟如何?至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去想象。(以上为第五章)
本篇叙事蕴含抒情,而抒情又与叙事紧密结合,二者水乳交融。这在前三章的叙事、第四章的追忆和末章的哀叹无不如此。
本篇在结构上十分讲究。铺陈叙事与抒情,层次既分明,又错落有致,步步加深,环环紧扣。反映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使久戍不得归而忧伤悲苦、怨恨满怀的兵士形象跃然纸上,从而体现了极高的概括能力与表现技巧。无论对进军备战场面的描写,对驻地军心涣散的铺陈,以及对离别时痛苦的叙述,无不情景逼真,委婉有致。正如陈子展云:“诗人若具速写之技,概括而复突出其个人入伍、出征、思归、逃散之整个过程。”(见《诗经直解》按语)。
击鼓
土国城漕③,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④,平陈与宋⑤。
不我以归⑥,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⑦,爰丧其马⑧。
于以求之⑨? 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⑩,与子成说(11)。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12),不我活兮(13)。
于嗟洵兮(14),不我信兮(15)。
【注释】①镗(táng):鼓声。②踊跃:跳跃。用兵:操练兵器。③土国:在国都兴建土木。城漕:在漕邑修筑城墙。④孙子仲:军队统帅名。⑤平:平定。陈、宋:皆国名。⑥以:犹使。⑦爰:语助词。居、处:住下来。⑧丧:丢失。⑨于以:在何处。⑩契阔:聚合。胡承珙《后笺》:“言死生相与约结,不相离弃。”(11)成说:订约。(12)于嗟:叹词。叹息声。阔:遥远。(13)不我活:不让我活。(14)洵:久远。(15)不我信:不让我守信用。
【鉴赏】这是士兵厌战思归之诗。
春秋时期,诸侯之间战争频仍。据《左传》记载,鲁宣公十二年,宋国攻打陈国,卫国出兵救援陈国。十三年,晋国不满意卫国救援陈国而出兵讨伐卫国。这可能就是此诗产生的历史背景。
全诗五章。一章写应征入伍。诗一开头就笼罩紧张的备战气氛。战鼓咚咚响,士兵们正在跳跃着操练刀枪。有的人在国都兴建土木,有的人在漕邑修筑城墙,而主人公却出征南方。二章写随帅出征。士兵们随从统帅孙子仲,去平定陈国与宋国的战乱。这场战乱虽然平息,但情势有变,仍不让士兵回家。为此,士兵们非常忧伤。三章写驻守待命。士兵们无可奈何,只得寄住异乡。由于军心涣散,情绪低落,连战马也丢失了,只好到林中去寻找。四章写夫妻离别。这是回想之词。在临别前夕,主人公与妻子发过誓言:死生与共;还拉着妻子的手说:与你偕老。而如今被迫分离,不能朝夕相处,怎不叫人牵肠挂肚。五章写厌战思归。主人公久戍不归,思家心切,他不停地叹息道:唉! 离家遥远,简直不让我活下去;戍时太久,硬是不让我守信用。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统治者的怨愤之情。
此诗全篇用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描写从军士兵的行为、心理和语言。文笔简练,形象传神。篇中写景若绘,篇末抒情真切。它不朽的艺术魅力永远地传达着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愿望。
击鼓
击鼓其镗,
踊跃用兵。
土国城漕,
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
平陈与宋。
不我以归,
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
爰丧其马?
于以求之?
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
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
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
不我信兮。
战鼓擂得冬冬响,士兵踊跃练刀枪。有的于国挖战壕,有的筑漕城,偏我远征向南行。
跟随将军孙子仲,和好邻国陈宋是为了伐郑。回老家偏我没份,使我心焦又伤痛。
行军掉队哪里停留哪里住?谁知在哪儿又丢了战马? 叫我何处寻找它?我呀找马来到山林下。
生和死都在一起,和你约定的话还记在心里。紧紧握着你的手,誓与你白头到老。
可叹如今相别离,不能回家与你团聚。可叹如今远离散,使得咱们誓约不能如愿。
《击鼓》五章,章四句。这是一首厌战诗。诗中充满了对统治者的憎恨,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幸福生活的憧憬。清方玉润《诗经原始》诗题序说:“卫戍卒思归不得也。”诗中叙述了士兵从入伍、出征以至思归逃散的经过。《诗序》:“《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多数学者都以为此诗是写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卫国统治者与陈、宋等国伐郑的战争。一说,此诗是写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宋伐陈时卫穆公出兵救陈的战争。如姚际恒《诗经通论》云:“此乃卫穆公背清丘之盟,救陈为宋所伐,平陈宋之难,数兴军旅,其下怨之而作此诗也。因陈宋之争而平之,故曰 ‘平陈与宋’;陈宋在卫之南,故曰 ‘我独南行’。”可备一说。
全诗五章。一章写击鼓练兵,真可谓一幅生动的备战图。二章写南行远征,诉说有家难归的痛苦心情。三章写思归逃散的情景,军心涣散,没有斗志,连战马都丢了,厌战情绪,由此可见一斑。《集疏》曰:“军士散居,无复纪律”四章回忆自己与妻子离别时的情状,想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清方玉润《诗经原始》眉评曰:“有此一章追叙前盟,文笔始曲,与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机局相似。”五章连用 “于嗟”反复咏叹,厌战反抗情绪可见。《击鼓》这篇诗是最古的以兵写兵的短篇杰作。又李蒲平所说:“此诗丧马求林,离散阔洵之状,千载如见。”又陈子展《诗经直解》中说:“诗人若具速写之技,概括而复突出其个人入伍、出征、思归、逃散之整个过程。简劲不懈,真实有力,至今读之,犹有实感。”
这篇诗在艺术成就上也是很有特点的。全诗寓情于事,叙事又有波澜。全诗以士兵消极厌战反战这一中心为线索贯穿始终。一、二章在叙事中发出“我独南行”、“不我以归”的怨言,表现其不愿南行参战。三章细写士气涣散情形,其厌战情绪不言而喻。四章追叙前盟,文章起伏迭宕,以反衬强化主题。五章以连用“于嗟”反转上意,转合一章“我独南行”不能如约之苦。变化开合,井然有序,将其厌战情绪写得淋漓尽致。清王先谦评之曰:“一时怨愤离叛之状可见!”其言甚是。
击鼓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爱居爱处,爱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询兮,不我信兮。
这首诗是一个远征异国、长期不得归家的士兵的控诉。关于诗的时代背景,古来说法不一。但从诗表达的思想内容看,反映了统治阶级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发动了无休止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第一章开头先声夺人,写击鼓进军,士兵们踊跃地操起武器训练,有的在国都内建筑房屋、城防工事。前三句就举重若轻,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战备图,活画出城内士兵紧张操练,漕地筑城的繁忙景象,烘托了战争爆发前的紧张气氛。同时又交代了“我独南行”的背景。“南行”是指下章说的讨伐陈与宋的战役。因这两国在卫国之南,所以说“南行”,写了士卒行军时心中所想,诅咒自己偏偏不幸被迫远征南方的噩运。吕东莱《家塾读诗记》引李氏说:“土国城漕,非不劳苦,而独处于境内,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虽欲为土国城漕之人,不可得也。”实乃征人之切身感受。第二章写南行之事,表达了有家难归的痛苦心情。前两句以赋铺陈,写自己跟随公孙子仲将军,讨伐平定了陈、宋两国。后两句抒情,他万般无奈地对天长叹: 为何还不让我们归家?! 难道打完仗还要让我们这些幸存者长期守边,我们这忧心忡忡的心都要碎了! 这一章没有展开描写平定陈、宋两国的战役,而是一句带过,详略得当,紧扣主旨,实写行役之苦、期限之长给征人心中带来的怨恨和忧伤。第三章是说“军士散居,无复纪律”(《集疏》),“缘上不得归而言之”(《义门读书记》)。在驻守的地方军心涣散,没有斗志,连战马都丢了,只有到树林中去寻找。厌战情绪,溢于言表。可见非正义的战争,就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第四章回笔倒述,追叙自己与妻子离别时的情景,想起和爱人的誓约:“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时立誓同死生离合,这些约定言犹在耳,而这一切现在都成了空话。这一段侧面描写,充满着难以生还的忧伤和士兵思乡怀人之愁,表达了对驱迫他上战场的统治者的憎恨。最后在第五章中,他不禁沉痛地诉说: 唉! 现在我们这些久离家人的当兵的,只怕今世不能活着回去了! 尽管当初临走时预先定下了回家的信约,今生是难以如愿了! 这一咏之叹,正如李蒲平所云:“此诗丧马求林、离散阔洵之状,千载如见。”这种委曲怨恨的典型情绪,正反映了人民对非正义战争的反抗。
周代初年,大小诸侯原有一千八百国,到春秋时代只剩三十几国了,诸侯间大鱼吃小鱼的兼并战争的剧烈程度,可想而知。此外,周人常常受到四夷的侵扰,抵抗外侮的战争便时有发生。根据史书记载,卫国对外战争也很多。《击鼓》这首诗反映的“平陈与宋”的战争,旧说是指鲁隐公四年 (前七一九) 卫联合宋、陈、蔡伐郑的事,但与诗中所写的情况不符,所以不可信。姚际恒认为是指鲁宣公十二年 (前五九七)宋伐陈,卫救陈而被晋所伐的事,可备一说。由于史书阙载,《击鼓》所反映的到底是哪次战争,很难确指,不必硬性附会史实。
这首诗无论是描写备战出征场景,铺陈军心涣散情况,还是叙述离别的痛苦,都情景逼真,文笔委婉有致。据陈子展《诗经直解》按语所言:“诗人若具速写之技,概括而复突出其个人入伍、出征、思归、逃散之整个过程。简劲不懈,真实有力,至今读之,犹有实感。”本诗为其短小篇幅和抒情性质所限,当然不可能象杜甫的《兵车行》或王昌龄的《从军行》组诗那样,详叙人民所受的战乱兵燹之苦。但是作者所具备的高度概括能力,不仅使这首诗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在艺术成就上也很突出。首先是寓情于叙事之中,无论前三章的叙述,还是第四章的回忆和最后的嗟叹,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前面的叙事中既有抒情,又为后面的呐喊呼号作了铺垫,主人公那种情调凄怆、思绪悲愤的形象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其次在叙述次序上错落有致,前后呼应,放得开,收得起,变化开阖,井然有序。第一章战鼓咚咚、甲兵踊跃的喧嚣气氛,给第二、三、四章的倾诉苦衷作了渲染底垫; 而二、三、四章的叙言,则进一步深化了第一段场面描写的思想内容,前后辉映,互相补充。同时,情节的发展与韵脚、句型的变换紧密结合,加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在前四章的铺陈之后,第五章一咏三叹,四个感叹词蝉联而下,累累如贯珠,朗读起来,铿锵和谐,掷地有声。至此,诗人的激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卫国统治者发动战争造成的罪恶也得到了深刻揭露。
《击鼓》这首诗不愧为一支杰出的士兵之歌。
击鼓
〔原文〕
击鼓其镗,
踊跃用兵。
土国城漕,
我独南行。
(镗、兵、行,阳部。)
从孙子仲,
平陈与宋。
不我以归,
忧心有忡。
(仲、宋、忡,中部。)
爰居爰处?
爰丧其马?
于以求之?
于林之下。
(处、马、下,鱼部。)
死生契阔,
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阔、说,祭部。手、老,幽部。)
于嗟阔兮,
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鲁韩洵作夐。)
不我信兮。
(阔、活,祭部。洵、信,真部。)
〔译文〕
战鼓擂得冬冬响,士兵踊跃练刀枪。有的于国挖战壕,有的筑漕城,偏我远征向南行。
跟随将军孙子仲,和好邻国陈宋是为了伐郑。回老家偏我没份,使我心焦又伤痛。
行军掉队哪里停留哪里住?谁知在哪儿又丢了战马? 叫我何处寻找它?我呀找马来到山林下。
生和死都在一起,和你约定的话还记在心里。紧紧握着你的手,誓与你白头到老。
可叹如今相别离,不能回家与你团聚。可叹如今远离散,使得咱们誓约不能如愿。
〔评介〕
《击鼓》五章,章四句。这是一首厌战诗。诗中充满了对统治者的憎恨,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幸福生活的憧憬。清方玉润《诗经原始》诗题序说:“卫戍卒思归不得也。”诗中叙述了士兵从入伍、出征以至思归逃散的经过。《诗序》:“《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多数学者都以为此诗是写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卫国统治者与陈、宋等国伐郑的战争。一说,此诗是写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宋伐陈时卫穆公出兵救陈的战争。如姚际恒《诗经通论》云:“此乃卫穆公背清丘之盟,救陈为宋所伐,平陈宋之难,数兴军旅,其下怨之而作此诗也。因陈宋之争而平之,故曰 ‘平陈与宋’;陈宋在卫之南,故曰 ‘我独南行’。”可备一说。
全诗五章。一章写击鼓练兵,真可谓一幅生动的备战图。二章写南行远征,诉说有家难归的痛苦心情。三章写思归逃散的情景,军心涣散,没有斗志,连战马都丢了,厌战情绪,由此可见一斑。《集疏》曰:“军士散居,无复纪律”四章回忆自己与妻子离别时的情状,想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清方玉润《诗经原始》眉评曰:“有此一章追叙前盟,文笔始曲,与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机局相似。”五章连用 “于嗟”反复咏叹,厌战反抗情绪可见。《击鼓》这篇诗是最古的以兵写兵的短篇杰作。又李蒲平所说:“此诗丧马求林,离散阔洵之状,千载如见。”又陈子展《诗经直解》中说:“诗人若具速写之技,概括而复突出其个人入伍、出征、思归、逃散之整个过程。简劲不懈,真实有力,至今读之,犹有实感。”
这篇诗在艺术成就上也是很有特点的。全诗寓情于事,叙事又有波澜。全诗以士兵消极厌战反战这一中心为线索贯穿始终。一、二章在叙事中发出“我独南行”、“不我以归”的怨言,表现其不愿南行参战。三章细写士气涣散情形,其厌战情绪不言而喻。四章追叙前盟,文章起伏迭宕,以反衬强化主题。五章以连用“于嗟”反转上意,转合一章“我独南行”不能如约之苦。变化开合,井然有序,将其厌战情绪写得淋漓尽致。清王先谦评之曰:“一时怨愤离叛之状可见!”其言甚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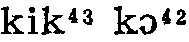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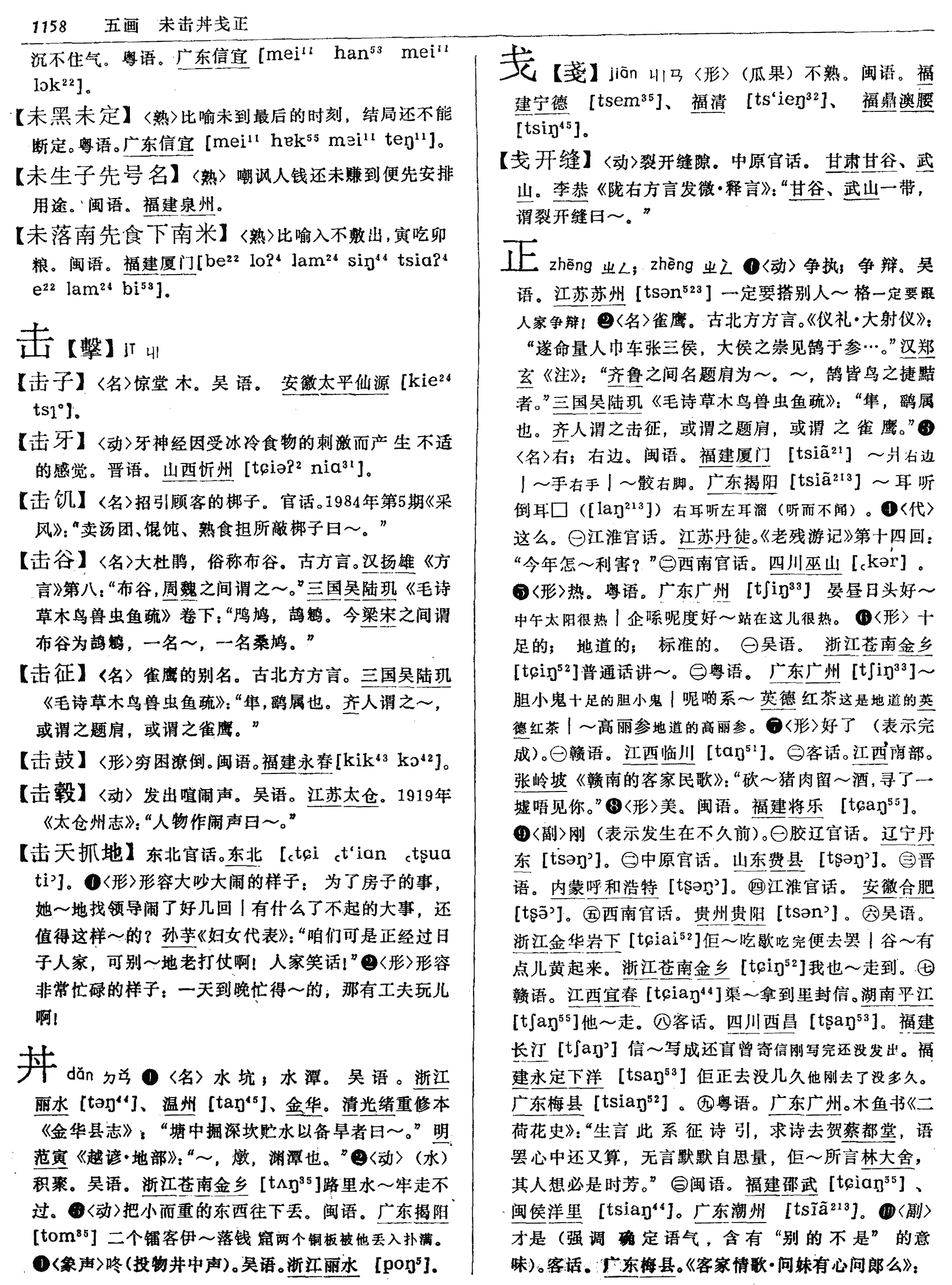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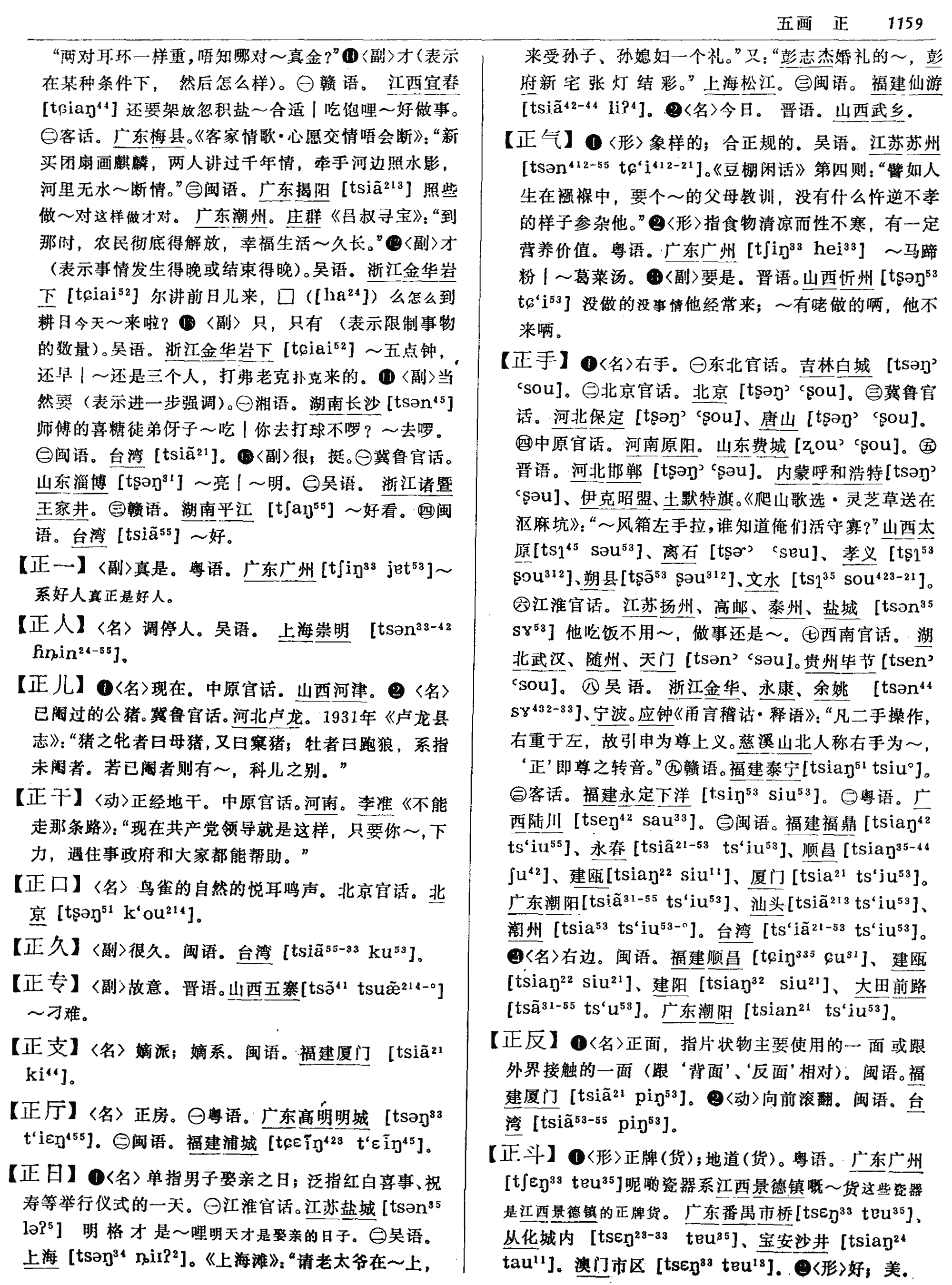
打鼓
鼓(敲鼓;鸣鼓;击鼓;擂鼓;挝鼓;伐鼓;拊鼓;负鼓;戒鼓;操鼓;摐鼓;椎鼓;捶鼓;打鼓;槌鼓;折鼓) 击革 擂鼙 雷鼓 发擂 鸣枹 发枹
击小鼓:鼓朄
敲锣打鼓:枞金伐鼓 扬锣捣鼓
击奏鼓乐:鼓曲
击鼓和奏乐:鼓乐
锣鼓的一种打击法:雨夹雪
击鼓召众:鼓征
击鼓聚集众人:鼓众
击鼓使进:鼓
击鼓行军:鼓行
擂出急促的鼓声:鼓严
另见:击打 乐器 鼓
- 入林把臂是什么意思
- 入柳是什么意思
- 入根是什么意思
- 入格是什么意思
- 入桂渚次砂牛石穴是什么意思
- 入档是什么意思
- 入梁子是什么意思
- 入梅是什么意思
- 入梅和出梅是什么意思
- 入梦是什么意思
- 入梦殊巫峡,临池胜洛滨。是什么意思
- 入棺是什么意思
- 入棺见妇是什么意思
- 入棺钉盖是什么意思
- 入楚岂忘看泪竹,泊舟自应爱江枫。是什么意思
- 入楚廉颇是什么意思
- 入楼早月中秋色,绕郭寒潮半夜声。是什么意思
- 入楼消酒力,当槛写诗题。是什么意思
- 入槛儿是什么意思
- 入檐蛇是什么意思
- 入次是什么意思
- 入款是什么意思
- 入步是什么意思
- 入武关是什么意思
- 入死出生是什么意思
- 入殓是什么意思
- 入殓前为死者穿衣化妆是什么意思
- 入殓前停放尸体的床铺是什么意思
- 入殓和出殡是什么意思
- 入殓埋葬是什么意思
- 入毛虎是什么意思
- 入气是什么意思
- 入气音是什么意思
- 入水是什么意思
- 入水下滑道是什么意思
- 入水不够垂直是什么意思
- 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什么意思
- 入水台是什么意思
- 入水捕兔是什么意思
- 入水摸月是什么意思
- 入水斋是什么意思
- 入水激一激是什么意思
- 入水管是什么意思
- 入水者异是什么意思
- 入水肢肿方是什么意思
- 入水见长人是什么意思
- 入水角是什么意思
- 入水试验是什么意思
- 入水问渔、入泽问童是什么意思
- 入汛是什么意思
- 入江巨川编是什么意思
- 入汤庭是什么意思
- 入沕古子是什么意思
- 入没头顶是什么意思
- 入河巨川编是什么意思
- 入河残日雕西尽,卷雪惊蓬马上来。是什么意思
- 入沾是什么意思
- 入法是什么意思
- 入法眼是什么意思
- 入泥不染争莲洁,倚月同香让桂开。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