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常引
词牌名。一名《太清引》、《腊前梅》。双调四十九字,上阕四平韵,下阕三平韵。又一体五十字,惟上阕第二句增一字。又曲牌名。北曲入仙吕宫,字句格律与词牌上阕同。参见“常用词谱”类。
太常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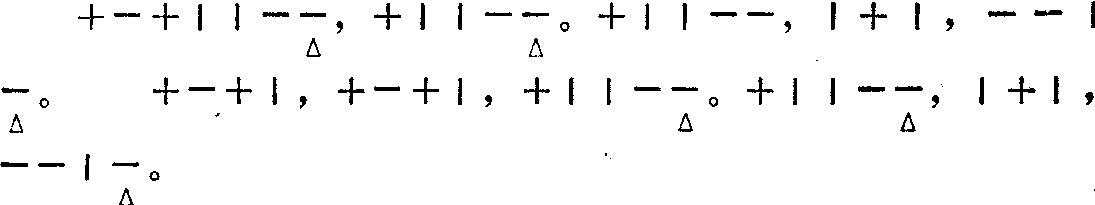
太常引
又名《太清引》、《腊前梅》。见宋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云:“京师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烟》等,号‘唐赞’。”则此调在宋亦用于佛曲。《词律》卷五列之。《词谱》卷七列辛弃疾“仙丛似欲织纤罗”一首,双调,四十九字,上片四句四平韵,下片五句三平韵。又列高观国“玉肌亲衬碧霞衣”一首为另体,高词比较辛词,唯上片第二句由五字句改为六字句,馀略同。
太常引
饯齐参议归山东
故人别我出阳关,无计锁雕鞍。今古别离难,兀谁画、蛾眉远山? 一尊别酒,一声杜宇,寂寞又春残。明月小楼间,第一夜、相思泪弹。
此词作者为燕山(今北京)一歌妓,善作小词。所欢齐参议(名字、生平无考,“参议”是官名)归山东,她作此词赠行。短短数语,明白晓畅,然作者之深情厚意,却表现得婉曲刻挚,如泣如诉。
开篇化用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西出阳关无故人”句意,以此构定送别的主题及其格调。“无计锁雕鞍”,既写缠绵悱恻之情,又状无可奈何之态。因情深,故欲锁雕鞍,不放所欢远行;因其必去,故又无计可施。正是在这种欲舍情牵、欲止不能的矛盾心理支配下,进而发出“今古别离难”的深刻感叹,将眼前的离别之情蓦然推扩,表现了悲剧性的今古别离之痛的永恒主题。而总括千古之离情别恨,仅以此一平淡语出之,尤见相反相成之效。“兀谁画、蛾眉远山”,跳开一层,以无心画眉之慵懒之态,写出索漠心境。
下片承前别意,进而刻划入微。“一尊别酒,一声杜宇,寂寞又春残”,正对酒饮别,忽听若“不如归去”之杜鹃啼声,当此“春残”之际,离愁别恨更何能堪?“明月小楼间,第一夜、相思泪弹”,以预想作收,撷取别后“第一夜”的情感冲突的高峰,以极简语涵括极丰富的情感活动,是“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李白《三五七言诗》)之自伤呢,还是“相思难表,梦魂无据,唯有归来是”(欧阳修《青玉案》)的期待?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令人咀嚼不尽。
太常引
这是一首言情小令,极写相思之苦,塑造了一个情深意笃的思妇形象。上片叙事,下片写情,人物行动与内心的写照,前后补充印证,浑为一体。首两句点明时光和环境。时间在中午,主人公正在午休。画面一片清丽,爽风阵阵,透过碧青色的纱帐,竹席生凉。这样的环境氛围,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十分安适惬意的,但却不然,作者笔锋一转,纳入正题,突出交代了主人公“独自守空床”的孤寂处境。她正经受着相思的煎熬。痛苦的泪水,串串流下,无休无止。李清照《南歌子》词“凉生枕簟泪痕滋”,刻画悼亡的悲哀。这里化用其意,但笔触从含蓄转为明快,扩充了词句的容量,使情感单一化而又铺展开来。一般描摹愁思,往往选取能够造成凄清神思的景物,以渲染气氛,为写愁作铺垫,多写夕阳芳草,残荷败柳,斜风细雨,等等不一。这首小令不同,虽然同样是以景寓情,却未采用习见的熟套手法,而是另辟蹊径,极写外界景致的美好。“都是好风光”的室外景象,显得与主人公“独自守空床”的心理状态非常不协调,但正是在这种对立的不协调描写中,反衬出主人公无法排遣的痛苦。风光永昼,度日如年,令人倍受折磨。反衬手法的运用,有时比正面映衬更有力量。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上)是也。
下片推进一层。前三句实写主人公所思念的内容:离别时情意缠绵,不忍割舍,相互叮嘱,约定早日相聚,决不负心食言。所有这些“言笑晏晏,信誓旦旦”的情景,历历在目,女主人公曾经铭记肺腑,无论怎样也不会淡灭,因此也就格外痛苦,现在想挣脱这种感情的困扰,硬要自己不把它放在心上,又如何能办得到呢?“刚道”,是“偏说”、“硬说”的意思。张先《菩萨蛮》词:“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恼,刚道花枝好。”苏轼《水调歌头》词:“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都与此处的“刚道”同义。这一吞吐顿挫之笔,把主人公无时可消、无计可除的刻骨愁苦揭示得淋漓尽致。“不是不思量”三句,用反接语来诠释上一句的设置,补足了上文的潜台词。不是不思量,而是不堪言、没法说。“教人语长”中隐伏着一个“怕”字,这与宋人张未《风流子》词中“情到不堪言处,分付东流”的意思相似。这个结句,可以引起读者的诸多想象,似实非实,深具有余不尽之妙。
这首小词的最大特点是质朴自然,不事雕琢。字面意思看来坦露浅易,而内涵却相当深刻,感情的起伏,一波三折。浅语深情,是为词家本色。词这种抒情诗样式,原本来自街陌谣讴,清新活泼,率直坦露,如《敦煌曲子词》一类;但到了文人手里,渐趋隐曲雕饰,往往失却白描之美。杜仁杰生活在宋末元初,是词作逐渐衰微的时代,代词而起的散曲,返朴归真,作品的生活气息又浓烈起来。杜仁杰本人是散曲家,《录鬼簿》把他列在“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栏内。他作长短句,词的风格虽并未走样,但却也受到散曲写作的影响。这种以曲入词的笔调,别具一格,特别引起读者的兴味。
太常引
这是一首摹拟女性口吻写思妇怀人的小词,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季节。上半写景,下半叙事抒情,是这类小词的传统结构,但写景言情都有独到之处,值得玩味。
“弄晴微雨细丝丝”,一起奇绝。微雨象是有意在晴天里玩弄自得。写的是天已晴了,却有丝丝细雨未全消失。“弄晴微雨”虽是秦观《水龙吟》里的成句,但缀以“细丝丝”三字。莫小看这细丝丝的微雨,却有很大的能量。平时多姿多态的秀媚山色,被细雨遮得黯淡无光,只有淡淡的山形而已。“山色淡无姿”五字把这种景象写得如在目前。赵孟頫是著名的画家,“弄晴”两句写景亦如一抹平远山水。但这画面诉诸读者的是怅惘之情。试想,明媚多姿的山色现在变成“淡无姿”,岂不大煞风景?词中人的视线透过微雨眺望山色,落得个“淡无姿”的感受,遂将目光收到近处的庭院。“柳絮飞残,荼䕷开罢,青杏已团枝。”春天已经完了。柳絮暮春始飞,现在飘飞殆尽;荼䕷是春末夏初的花卉,现在也开完了。这是以已消失的景物来表现春光的逝去。青杏已一颗颗出现在枝头,这是以正在成长的初夏景物写春事已空,和前八字虚实相映。苏轼《蝶恋花》说:“花褪残红青杏小,……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同是写春去夏来,苏词飘逸自得,赵词却触物兴怀。试看“无姿”、“飞残”、“开罢”,总是令人惆怅。这上半阕虽然全是写景,但情绪已经注入景物,与过片意脉潜通了。
词中人为什么会如此惆怅?“栏干倚遍人何处”一句道出了原因,领起下片。原来以为春天总可与丈夫团聚,但春已尽而行人却杳无归期。倚遍栏干,望断天涯,人儿究在何方呢?这七字将一腔愁绪都倾泻出来。“遍”字尤其着力。倚栏之际,不时听到黄鹂对语的鸣声。黄鹂尚可对语谈情,而自己却孤独无偶,故曰“愁听”。“恨别鸟惊心”,杜甫早已有此体会了(见其《春望》诗)。“栏干倚遍”、“愁听语黄鹂”,在庭院里觉得很无聊,那么室内又如何呢?“宝瑟尘生,翠绡香减”,表明分别已经很久了。因为无情无绪而多日不弹的宝瑟蒙上了灰尘,熏透的翠绡香味早已经减退,也无心重熏。恹恹若此,总为相思念远之故。末句更用重笔再次揭出此旨:行人远在天涯,音信全无,教人何以为怀!妙在很含蓄地下了“天远雁书迟”五字。云路遥遥,传书的大雁迟迟未至,然而再迟也总有来的时候罢?思妇还在痴痴地期望着。
这首小词无论写景或叙事言情,都是有远有近,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笔端开合有势,决不平铺直叙。又蕴藉幽怨,令人涵泳不尽。
太常引
这是一幅画,构图十分别致:远处是依微隐约的山色与白云。占据画面主要空间的是万竿修竹,亭亭玉立,娉娉袅袅,似绿衣少女,似倚翠美人。近处是几枝新篁嫩箨,摇曳于苍苍梧桐之下,长幼相依,相映成趣。更妙者,此图景中有景,画中有画:画面之一角,微露楼阁,西窗绿纱,洒上斑驳树影,又成一纸绝妙横幅,天然造化,不烦人工。此可谓构图之高手。
这又是一幅水墨画,以青绿为底色,十分幽雅。画面墨色之搭配,有淡有浓,有枯有润:淡淡的山光云影与浓绿重翠之竹林相辅相成,新篁之嫩颜与苍梧之老色相反相济,隐隐树影与青青帘栊相即相融。作者墨分五彩,用色精审,而整体上色调和谐,意境统一,只见满幅青光,一派绿意。此可谓用墨之高手。
这也是一幅有声画,它用诗的语言构成,在时间的推移中展开。墨作的画,只能是静态的无声画,只可选取时间中的一个点,描绘一瞬间凝固了的空间;这幅画却是有色,有声,有空间的广度,也有时间的长度。且听声音:轻风吹拂竹林,如传私语,不绝如缕;新篁摩挲苍梧,如搔痒处,忍俊不禁;间有树叶飘坠,枝扫窗纱,何处不是天籁,何时无有妙音?再看时态:腻香春粉,万竿亭亭,露压烟啼,清泪如倾,此晨光未露时也;云淡风轻,崇光泛泛,苔痕上阶绿,山色入帘青,此午日映照时也;赤乌西斜,落日反照,满庭清幽,影横小窗,此黄昏夕曛时也。一日之内,一院之景,画面之不齐若此,作者一一摄入画框,此可谓写生之高手。
这更是一幅“心画”,作者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因情而设景,随意而遣墨,笔下景物多为精神之写照,人品之象征。如亭亭之竹,虚心有节,处世得道,不闻人称“竹君子”乎?又如午日之景,云淡风轻,一切都是如此安闲,没有造作,没有苛求,正如文人雅士淡泊宁静之生活态度。再看“新篁摇葆,苍梧张盖”两句,“葆”指“羽葆”,是用鸟羽装饰之车盖,多为王侯贵族所用,这两句字面含义是:新竹凤尾森森,如鸟羽之饰,苍梧广张法轮,如车驾之盖。而内在含意则是:游于新竹老梧之下,安步当车,自有乐天知足之心,无须高车驷马之求。还有“山色入帘青”化自刘禹锡《陋室铭》,其意向所指不言而喻。总之,画面景物处处渗透着作者之精神、气质。此可谓“写意”(写胸中之意)之高手。
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在于道通为一,融合流布。“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此词正体现了如此精神,故以品画之法读之。
太常引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众生变相,层出不穷。但古往今来,也有一些“共时性”的东西存在。以交友之道论,既有倾盖如故、风雨同舟者,也有趋炎附势,锦上添花者,真个是达在深山有客访,穷处闹市无人问。词人有感于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写下了这首词。
“青山憔悴锁寒云,歧路上,最伤神。破帽鬓沾尘,更谁是、阳关故人?”这是一幅凄凉的图景,主人公身处困境,落拓不遇,面临歧路,徬徨无主。既没有人鼓吹喧阗,设宴相送,也没有人执手相看,泪眼相向。因为穷困,这个世界已把他遗忘,任其踽踽独行,形影相吊。唯一相看两不厌的,是远处的青山,而且这青山也被云遮雾锁,憔悴不堪。反观自身,更是伤心:破帽遮颜,两鬓蒙尘,一副寒酸相。在这种潦倒穷愁的境地里,最需要的就是朋友的安慰了,哪怕是一句话,一杯酒,也会使人铭感终身。当年王维曾写过一首《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作流露出的真情远虑,真使人感动得唏嘘泪下。但是,茫茫人海,如今又有谁具备这古道热肠,来为我送行呢?写到此,词人真正感到了一种莫名的伤感,世道啊,你太浇薄!世人哪,你太势利!
词的上片偏于伤感,而下片则转为愤怒。笔调也由感叹转为嘲讽:“颓波世道,浮云交态,一日一番新。无地觅松筠,看青草、红芳斗春。”杜甫诗《可叹》云:“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后人常以白云苍狗比喻世事之变幻莫测。词人深有同感。眼见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昨日里骏马换酒,高朋满座,今日里千金散尽,宾客绝迹,这些酒肉朋友,真是一天一个面孔。结尾处,词人见眼前红芳斗春,倍增感叹,景与眼谋,外与内合,遂将情景化合一处,以“现量”之景来暗寓人世之事:你看遍芳郊姹紫嫣红开遍,争奇斗艳,各逞风流,乱纷纷,闹烘烘,攒聚一处,犹如那世间小人,巴结权门,抢占高枝,你争我夺,你拥我挤,全没些儿骨气。再找那岁寒之友,觅那松竹高风,却全不见踪影。这真是衰败的世道,颓废的人心啊!
凭心而论,世态炎凉何时不存,何处不有,但富贵亨通者视而不见,飞黄腾达时听而不闻,唯有在生活的底层,才能最深刻地体会到这种阶级社会中畸形的人情关系。作者心既感之,笔复记之,为我们留下了一篇以议论为主、入木三分的词作。
太常引
端阳日当母诞不得归(二首)
彩丝堂上簇兰翘,记生母、在今朝。无地捧金蕉,奈烟水、龙沙路遥。碧天迢递,白云何处?风急雨潇潇。万里梦魂消,待飞逐、钱唐夜潮。
短衣孤剑客乾坤,奈无策、报亲恩。三载隔晨昏,更疏雨、寒灯断魂。赤城霞外,西风鹤发,犹想倚柴门。蒲醑漫盈樽,倩谁写、青衫泪痕?
陈孚的《太常引》共两首,最早见于明杨慎《词品》卷五:“天台陈刚中孚在燕,端阳日当母诞,作《太常引》两首云(词略)。时为编修。”经笔者考证,陈孚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入京,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二十九年(1292)三月至八月,扈从世祖巡幸上都(故址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此年作诗有“三年去乡井”(《出建德门赴上都分院》)、“燕子三见归”(《李老峪闻杜鹃呈应奉冯昂霄》)等语。观词中“龙沙路遥”、“三载隔晨昏”云云,可知亦当作于是年端阳节,时信其母寿诞日,因远在上都,不得归乡亲祝母寿,故有此作。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言词为奉使安南(今越南)作,非是。
这两首词极为生动地抒写了天涯游子对母亲的深深思念,但艺术构思、章法布局各不相同。下面我们先谈第一首。这首词采用顺叙结构,完全按照感情的发展顺序来遣辞谋篇。开头两句是作者想象家中亲人在故乡为母亲祝寿的情景,句序应倒过来理解,即“记生母、在今朝。彩丝堂上簇兰翘”。彩丝,古代端午节,有用五彩丝线装饰厅堂、缠系手臂的风俗。据说五彩丝线象征五龙,五龙在室在身,可以辟鬼邪,保平安,故又名“长命缕”。兰翘,指母亲及家中其他女眷所插戴的华美首饰。这两句是说:端阳佳节,正是母亲的生日。寿厅上彩丝缭绕,家人亲眷们济济一堂,正按照传统习俗为她老人家拜寿。接下来两句,句序也应倒过来理解,即“奈烟水、龙沙路遥,无地捧金蕉”。金蕉,亦称“金蕉叶”,是一种底托为蕉叶形的酒杯。这两句说自己宦居在外,和故乡隔着千里沙漠、万重烟水,又公务在身,竟不能够返乡亲自向母亲祝酒。它们直点出词题中的“不得归”,并在行文上形成一大曲折,使家乡亲人为母亲祝寿时的喜气洋洋与异地游子不能到场的孤寂痛苦,形成鲜明的对比,感情色彩十分强烈,无可奈何的郁闷和怅惘跃然纸上。
过片意脉不断,承上“路遥”之意。“碧天迢递,白云何处”暗用唐代狄仁杰望云思亲的故事,寄托自己对母亲的深切思念之情。《新唐书·狄仁杰传》:“仁杰登太行山,反顾,见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亲舍其下。’瞻怅久之。云移,乃得去。”这两句对上片三四句之意作反复渲染,进一层地强化了思念母亲的赤子之心。按陈孚对其母极为孝顺,宦游在外,无时无刻不思念之,发于诗有“最愁亲舍远,梦绕白云边”(《感怀呈庞夷简修撰张幼度应奉二首》)、“老母越南垂白发,病妻燕北寄黄昏”(《江州》)等句,可与此词互相印证、阐发。接以“风急雨潇潇”一句,景中见情,含意蕴厚。一是描写了塞外恶劣的天气;二是点明风雨夜思亲之事;三以风狂雨骤之凄凉的物境,反衬出自己悲伤痛苦的心境。思亲已苦,而风雨夜思之,倍见其苦。然词人却不直言,而是借眼前景物自然显现,笔法何等深婉。最后两句,又作一层转折,另翻出进一层的深意,把思母之情推到了最高潮。“万里梦魂消,待飞逐、钱唐夜潮”。钱唐,指钱塘江,在今浙江杭州市,离词人故乡不远。这两句是说,尽管王事鞅掌,身不由已,但思念母亲的那一颗心,却非千山万水所能限隔,在梦中,我的魂魄定将追赶上钱塘江的潮水,连夜飞到母亲身旁。有此一结,作者的乌鸟之情,凸出纸上,溢出言表了。
这首词情真意切,愈转愈深,把那种普通而伟大的人性美——儿子对母亲的热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备足无余,千古之下。读之犹使人心旌摇摇,允推佳作。
第二首与前一首系同时而作,但艺术构思迥然不同。它采用对比映衬,虚实相间的手法,使词的意蕴更为深婉、丰厚,词情亦显得更为真挚感人。上片从己方着笔,基本上概括了前一首的全部内容,突出表现了自己孤旅他乡,不能报答母亲哺育之恩的痛苦。起句“短衣孤剑客乾坤”,直点出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游子身份。短衣,即短后衣,原是古代剑客的一种装束,这里泛指游士的衣着。“孤”字言其远离亲人,形影相吊。“客”字写其宦游他乡,萍泊蓬飘。正因为是天涯宦游人,所以身不由己,没有办法在母亲身边侍奉,报答养育之恩。“奈无策、报亲恩”二句极自然地流出笔端,词到,情到,意到。此句可以视作这两首词的主旨。也正是在这一年,陈孚曾向朝廷提出外放的请求,欲回乡就近任职,但终未获准。其诗有云:“万里家书到,催归未得归。山妻愁掩袂,稚子病牵衣。客舍园林僻,官曹簿领稀。清时鸳鸯满,容得一鸥飞?”(《至元壬辰呈翰林院请补外》)正是“奈无策”的一个例证。接下去两句为进一层的写法:“三载隔晨昏,更疏雨、寒灯断魂。”晨昏,古人侍奉父母的一种礼仪。《礼记》:“凡为人子之礼……昏定而晨省。”即晚间服侍父母就寝,早晨向父母省视请安。这两句是说:宦游他乡已经三年了,三年来不能侍奉母亲,尽晨省昏定的天职,每念及此,心中便十分难受,更何况是在此凄风苦雨的寒夜!一“寒”字用移情法颇见其妙。灯光自然不会“寒”,“寒”的仍是心境、环境。心寒,夜寒,才觉灯寒。“疏雨”、“寒灯”、“断魂”三个意象造成一种沉闷抑郁的环境和感情氛围,使“奈无策、报亲恩”的孝子心态得以具体而清晰的裸露。下片换头三句,宕开一笔,转从母亲一方来写:“赤城霞外,西风鹤发,犹想倚柴门。”“赤城霞”化用晋孙绰《游天台山赋》“赤城霞起而建标”句。赤城,文学作品中常以代指台州及临海地区,盖此地南朝梁时为赤城郡(因赤城山而名)。鹤发,即白发,言其母年事已高,同时暗喻其母日夜思念在外的游子,愁白了头。“倚柴门”用《战国策·齐策》典,王孙贾母曰:“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写母亲望子归乡。这三句用虚笔写作者的想象,形象地再现了母亲对自己的挚爱,同时也反跌出自己对母亲的深情。作者在诗中也曾直接写到这种情怀:“慈母年高鹤发垂,乡书无雁到家迟。初过寒时一百六,一日思亲十二时。”(《清明日感事》)末二句重新拍转自身,扣住“端阳日当母诞”之题,点出自己不能亲自向母亲敬酒祝寿的无比痛苦的心情:“蒲醑漫盈樽,倩谁写、青衫泪痕?”蒲醑,指端阳节饮用的用香蒲泡制的酒。“青衫泪痕”化用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诗意。这两句言自己所在的官府,也正在设宴庆贺端阳节,蒲醑酒酌得满满的,溢出了酒杯,但我却无心饮用。想到今天是母亲的寿诞日,自己不能侍奉在侧,内心十分痛苦,热泪沾湿了衣襟。有谁能够理解并写出此时此刻我这游子思念母亲的痛苦心情呢?以问句作收,见出此情无人慰藉,众人皆乐佳节而己独悲思亲,其凄恻即格外难以为怀了。
对母亲深深的爱,是天下赤子的共同感情。母爱是崇高、伟大、纯洁的,是报答不尽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孟郊的《游子吟》早就唱出了一曲动人的母爱赞歌。其后四百多年,陈孚这两首《太常引》词,以别样风采,再次向世人昭示了拳拳赤子之心。词人“把亲身感受过的一些情感移交给旁人,使旁人受到这些情感的感染”(托尔斯泰《论艺术》),无半点做作,无丝毫刻琢,充分显示了其所创作“任意即成,不事雕斫”(《元史·陈孚传》)的艺术特点。词中所表现的这种热爱母亲,报答亲恩的孝顺之心,体现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美德。文学史上以此为题材的名作,李密《陈情表》驰骋在前,孟郊《游子吟》趋之于后,得陈孚《太常引》词,真可鼎足而三。论体裁有诗、文、词之别,其并传不朽则是一致的,堪称殊途而同归了。
太常引
饯齐参议归山东
刘燕歌乃元时妓女,从此篇词意看,她与齐参议当有恋情。据《青楼集》,此词在元时脍炙人口,传唱一时。
上阕写饯别时情景。“故人别我出阳关”,用王维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送元二使安西》)意。“无计锁雕鞍”,反用柳永词“悔当初不把雕鞍锁” (《定风波》)意。二句妙用成语,写想尽办法,终于无计留住行人,只得设酒饯别。三、四两句对景增情。“今古别离难,兀谁画蛾眉远山”,依依携手惜别,古今本已难堪,再加上远山妩媚如画眉,更加撩人愁怀。“兀谁”是俗语,摹写无端嗔怪、无理有情之态,极其生动。前二句文雅,后二句俗白,却自然无间,相映成趣。
下阙设想别后相思之情。“一尊别酒”饮过之后,行人即将上路。杜鹃啼声仿佛在催促 “不如归去”,“一声杜宇”即暗寓 “归山东”意。“寂寞又春残”,别后本已寂寞孤独,又恰逢暮春时节,满目残花,伤春伤别,情何以堪。“明月小楼间,第一夜相思泪弹”。结尾两句又翻进一层: 别后春残,虽然难堪,但第一难遣却是月夜小楼之相思。明月小楼,本是传统相思意境,不足为奇;但因后一句句法新奇,突出强调“第一”二字,就显得情真意浓,楚楚动人。
全篇感人之处,正是在 “真情”二字,词人只是说她心中话、胸臆语,并未多加渲染雕琢,却令人觉得含蕴深厚,体味不尽。
太常引
一杯聊为送征鞍。落叶满长安。谁料一儒冠,直推上,淮阴将坛。 西风旌旄,斜阳草树,雁影入高寒。且放酒肠宽,道蜀道,而今更难。
这是首送别出征友人的词。
其起笔直书 “一杯聊为送征鞍”,既叙事,又入情,不像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维 《送元二使安西》)不像 “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陈亮 《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 。前者从描写景物入手,刻画出一个艺术环境,将惜别之情藏在其中,后者从叙述政治环境、赞美行者入手,将慰勉之意喷薄而出。这惜别与慰勉又正是这一类题材中两个主旋律。这首词先在首句用一 “聊”字,聊表寸心,见饯别,说无可奈何心情,是“惜”。结尾用“道蜀道,而今更难”,说此去前程的坎坷,是对友人的担心,也是 “惜”。这种 “惜”的表达渗透着一种对于人生的失望,前一个 “聊”字,说个人无奈,是对自己,对友人无法实现长期相聚的失望; 后一个 “难”字,铺向社会,指出社会比过去更为复杂、更为艰难的现实。这是对前途的失望,这又是对人生认识趋向于颓废的典型意识。“麯埋万丈虹霓志,醅淹千古兴亡事。”当然,造成这心理状态与当时异族统治的空前残酷分不开。
中间注意塑造艺术气氛,注意情绪的跌宕起伏。上片插入 “落叶满长安”, 用成句 “秋风吹渭水, 落叶满长安”, 点时令, 渲染气氛, 不似写景,又似写景,用在叙事文字中间增加了文字的姿态。下片“西风旌旄,斜阳草树,雁影入高寒”,三组形象画面是立体的,上是雁影,远是斜阳,中是旌旄,是写实,斜阳、西风、高寒,又具有象征性。“且放酒肠宽”,用 《十国春秋》周维岳饮酒特多故事,更是用 “劝君更尽一杯酒”诗意,表惜别,是全篇“诗眼”。这些全部围绕一个“惜”字。但描写“惜”字时,又不是一笔到底的感伤。除了开头、结尾逐渐拓展的深沉伤感外,中间“谁料一儒冠,直推上,淮阴将坛”,是赞美行者,是写实,对于全诗的感情却是兴奋的变奏,是哀曲中的骀荡之音。这是个人特色。
太常引
这是一首为友人祝寿的词。上片开头两句,词人着意描绘了隐居的优雅环境。“柳阴濯足水侵矶,香度野蔷薇。”在门前柳阴之下清澈的小溪边洗一洗脚,荡起的水花把溪边的石矶都浸得湿漉漉的。这是多么的凉爽、惬意! 一阵阵浓郁的野蔷薇的芳香扑鼻而来,真是沁人心脾! 面对如此清新优雅的环境,作者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一个问题: “芳草绿萋萋,问何事,王孙未归?”这里化用了淮南王刘安《招隐士》的诗句“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原诗的本意是指山林“草木茂盛,麋鹿所居,虎兕所聚”,不可久留,“欲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见洪兴祖《楚辞补注》)。但从谢朓的《王孙游》诗开始,皆反其意而用之,多指家乡绿草丰茂,正该及早归隐。这里也是如此,意思是芳草这样的茂盛,环境这样的优美,还有什么事情不能丢开,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留恋,为什么还不赶快隐居来享受这种清福呢?充分地表现了作者对隐居生活由衷的向往之情。
下片则进一步描写隐逸生活的悠闲快意。“一壶浊酒,一声清唱,帘幕燕双飞。”这里没有灯红酒绿、酒池肉林的奢华,只有一樽浊酒; 没有浓妆艳抹、踏筵狂舞的绝代妖娆,只有一声声清脆悦耳的歌唱; 没有猜拳行令、阿谀恭维的尘世喧嚣,安静得连燕子都能优闲自得地在帘幕间成双成对地飞来飞去,然而,却又别有一番情趣。“帘幕燕双飞”,也象征了夫妇间的和美。夫唱妇随,鱼水和谐,安然共享天伦之乐。这几句形象生动地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悠闲适意的隐居生活画面。“风暖试轻衣,介眉寿,遥瞻翠微。” 最后点题,向主人祝寿。天气又渐渐暖和起来了,正好脱去臃肿的冬衣,试一试轻薄的春衫。遥望远处,已是一片青翠幽深。我这里祝福你年年岁岁永远长寿,永远年轻!
况周颐 《蕙风词话》 评此词云: “寿词如此著笔, 脱然畦封, 方雅超逸,‘寿’ 字只于结处一点,可以为法。”的确也是如此,一般祝寿的诗词,往往免不了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地祝福主人富贵荣华、福寿康健、儿孙满堂之类的俗套。这首词却不然,作者的笔力着重在描绘隐逸生活的自在舒适,只于末尾用 “介眉寿”三字,淡淡提及祝寿之意。形象、自然地表达了词作者希望主人远离尘世嚣嚷,及早恬退隐居颐养天年的良好祝愿,显得志趣闲雅,意格高远。
太常引
此词约作于词人归隐之初。至元十九年(1282),刘因应朝廷之征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到任不久即辞官归隐。究竟词人受到了什么刺激,变得厌恶官场,看破人生,我们不得而知。这首词所流露的情绪,乃是一种对人生的顿悟;也可以说是对勋业功名的“读书人一声长叹”(元张可久《卖花声·怀古》)。上片分为两层。起三句:“男儿勋业古来难,叹人世,几千般。”突兀而来。以沉重、悲凉的感慨和大彻大悟唤醒全篇,是为第一层。“男儿要为天下奇”,欲济苍生建勋业,在词人看来已属无谓;负此志而最终一事无成,难免惆怅失意,更是执迷不悟。古往今来几人垂名千古?几人名成功就?——此乃词人千回万转参悟所得,故第二层紧接写大梦初觉,补出感慨的缘由。觉,醒来。邯郸梦,即黄粱梦,典出唐人传奇《枕中记》。词人功名勋业之梦惊醒,把虚浮无定的人生看得更加轻易,更加淡漠了。上片二层采用逆入写法,先发惊叹,继写惊醒,便觉雄奇突兀,不同寻常;如果倒过来写,虽合逻辑顺序,味道就淡多了。
大彻大悟之后便是无所追求、无所期待、随遇而安的心境。下片描写自己的隐居生活,亦分为二层。过片三句,词人经历了梦醒、参悟而发浩叹之后,终于觉得人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汲汲追求,还是深藏不出,与青山为伴,“相看两不厌”,下不与世俗红尘相接,上复有白云缭绕遮护,大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唐贾岛《寻隐者不遇》)的隐趣。但是,隐居又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动机:一种是陈抟式的,一种是谢安式的。陈抟是宋初著名隐士,隐居武当、华山,服气辟谷。宋太宗召他入朝,他飘然而至,又飘然还山,是真隐之士。谢安是东晋孝武帝时的宰相,入朝执政前,曾隐居于会稽东山。当其山居之时,就已经知道自己免不了要出任要职。他的隐居不过是一种等待。词人既已于过片坐实了隐士的身份,又担心被“不知我者”误指为待价而沽的假隐士,故末二句郑重声明:诸君千万不要将我错比谢安!淡语拙笔,情趣盎然,令人忍俊不禁。清代刘熙载《艺概》评刘因词云:“东坡谓陶渊明诗臞而实腴,质而实绮,余谓元刘静修之词亦然。”看似枯瘦而实际丰腴,看似质木无文而反复品味后却觉得文彩飞动,正是这首词的特色。
太常引
暮 行
栖鸦去尽远山青,看暝色,入林垌。灯火小于萤,人不见,苔扉半扃。照鞍凉月,满衣白露,系马睡寒厅。今夜候明星,又何处,长亭短亭?
这首暮行词可与作者《浣溪沙·早行》对读,一是壮游序曲,一是投宿愁吟,而《太常引》的写景造境尤胜于前者。
词以“栖鸦去尽远山青,看暝色,入林坰”起调,看似寻常无奇,而实能摄得暮行题咏神理,为以下迤逦入胜作地步.是善于发端的笔法。薄暮光景,归鸦争树、斜日沉汀的时刻已过去了,现在是林际昏鸦尽,原野阒无人,眼前但余一片晚山缀紫,这就自然引出了苍然暮色自远而至的景象。固然唐人词里就出现过“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的佳句,暝色之“入”并非新创,但用于此词却传达了更广阔的境界、更分明的层次感;暝色似雾如烟慢慢飘入客子所行的林野(坰,林外之谓)。看那黄昏暮色渐由浅而转深,日暮的客愁也由淡而增浓,夜幕完全从天宇落下,包围了大地,行人寻求栖宿的心情更切、脚步也更快了。暮行气氛笼罩了全篇。一路写下去,移步换形,又是妙境。“灯火小于萤,人不见,苔扉半扃。”《蕙风词话》卷三“益斋词不愧名家”条曾谓此等句“置之两宋名家词中,亦庶几无愧色”。灯火似萤,宋人笔下多有,陆游集中即见“一灯如萤雨潺潺”(《雨夜读书》)、“孤灯如秋萤,清夜自开阖”(《宿能仁寺》)等句。以萤比况灯光,本足以形容灯光的微小和光焰的闪烁;“小于萤”,则远火微茫、荒郊阒寂之境要突出得多,而描写的视角亦有所变换,确是行客眼中的见知和心中的感受。似此造语,未经人道。时明时灭的一点微弱灯火,依稀照见那将要投宿的处所:人迹杳然,门扉半掩(扃,关门;苔扉,门上生着苔藓,足见荒凉)。寥寥几笔,随手点染,画出了野驿荒村那种冷寂萧条的环境氛围。
下片接写行人歇宿的景况。这是一个明月白露、光影徘徊的秋宵。主人公解鞍系马,暂驻征程,四顾萧然,发现此地惟有寒厅可宿、凉月伴人。歇下来,清露满衣,空山独夜,旅魂何能安枕,疲躯怎得入梦!看来今宵大概只有耿耿不寐,默默愁思,待那启明星在天边出现了。明朝如何?“又何处,长亭短亭!”篇终再次拈出唐人《菩萨蛮》词“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的成句,稍加变化,着一“又”字,加重语气的不确定感,概括了前此旅途上的暮暮朝朝、山长水阔。“又何处”,与上句的“今夜”紧密呼应。明日关山路远,问谁同客子,跋涉中州!前道上,还有多少个十里五里、长亭短亭在等候飘泊者!这一结尾,蕴含着不尽情思。
太常引
莫将西子比西湖,千古一陶朱。生怕在楼居,也用着、风帆短蒲。银瓶索酒,并刀斫鲙,船背锦模糊。堤上早传呼:那个是、烟波钓徒?
这首词因友人新制画舫而引起想象,写景抒怀,寄寓了作者仰慕高士隐处山水间的情趣。
词的上片以范蠡携西子归隐五湖的历史故事衬托“浮家泛宅”主人厌于楼居,修制画舸,并首开湖船用布帆新例的隐君子形象。首句“莫将西子比西湖”,化用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句意,却又于句首冠以“莫将”,尤使其意曲折深婉。紧接“千古一陶朱”,将西子与范蠡联系起来,以其历史事实的内涵构成泛湖隐处的美妙意象。“陶朱”即陶朱公范蠡,史载范蠡与越王勾践深谋二十余年而灭吴,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遂携西子乘轻舟游五湖,变姓名自号鸱夷子,后父子治产至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以为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间行以去,止于陶(今山东定陶),人称陶朱公。这里不仅借范蠡之事为下文对隐处者的颂扬作垫笔,而且表达了对范蠡功成不居、疏财高蹈的饮羡之情。“生怕在楼居,也用着、风帆短蒲”,陡然落笔于现实之境,描摹漫翁潇洒情态。其描写对象,既与前述史事拉开千年距离,而相同的淡泊之志,又将现实之人与陶朱公之间的千年距离骤然凝缩,形成了超越时空的通感效应。
词的下片具体描摹画舫生活情态:饮酒斫鲙,自在逍遥。“银瓶索酒”,“并刀斫鲙”,“船背锦模糊”,动态和谐,色彩明快,构成一幅妙趣横生的图画。同时,图舫主人清俊的风骨、潇洒的气度也自然流溢出来。“锦模糊”,既为实景之锦绣交织,也是“索酒”之人醉眼中的朦胧幻象,上下天光,锦绣模糊,固有无穷浑灏之美,而词人心境沉溺其间,又自然逗发异想幻觉:“堤上早传呼:那个是、烟波钓徒?”烟波钓徒,唐代诗人张志和自号。张于唐肃宗时待诏翰林,坐事贬谪,后不复仕,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那个是”三字,明知故问,沉着厚重。以幻想作结,尤见情志之真。至此,“索酒”、“斫鲙”、的“钓徒”,在烟波浩淼之际更显现出离俗傲世的狂放形象。
张雨一生淡泊,年二十余出家为道士,往来华阳云石间,自称句曲外史。晚居茅山,罕接宾客,有云深不知之趣。故所咏吟,多“如深谷幽兰,苾芬远袭”(明顾起伦《国雅品》)。这首《太常引》,虽为漫翁而作,实亦有自喻之意。
- 十二户是什么意思
- (十二) 才情四溢 印外求印——赵之谦的多向探索是什么意思
- 十二把镰刀是什么意思
- 十二拜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结肠综合征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上部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下部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乳头影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内镜诊断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乳头测量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乳头炎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低张造影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内瘘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前门静脉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压迹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原发性肿瘤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双边征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周围异常韧带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壅滞症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壅积症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外瘘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导管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引流术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引流检查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引流液检查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悬肌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悬韧带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憩室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憩室梗阻性黄疸综合征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战伤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损伤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损伤分级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撕裂伤分类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旁疝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曲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曲扩大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梗阻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梗阻征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液和胆汁检查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淤积症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溃疡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溃疡急性穿孔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溃疡病压痛点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溃疡的内镜分期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溃疡的胃镜诊断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炎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炎的胃镜诊断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空肠吻合术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空肠曲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肠壁血肿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肿瘤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胃反流显像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腺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腺癌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营养液滴入法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血管压迫综合征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血管性压迫症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造瘘术是什么意思
- 十二指肠钩口线虫是什么意思